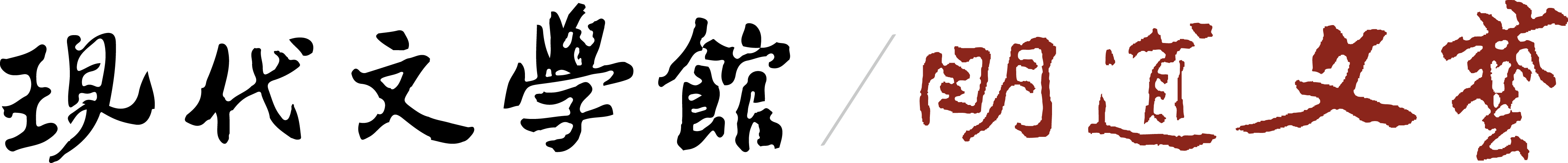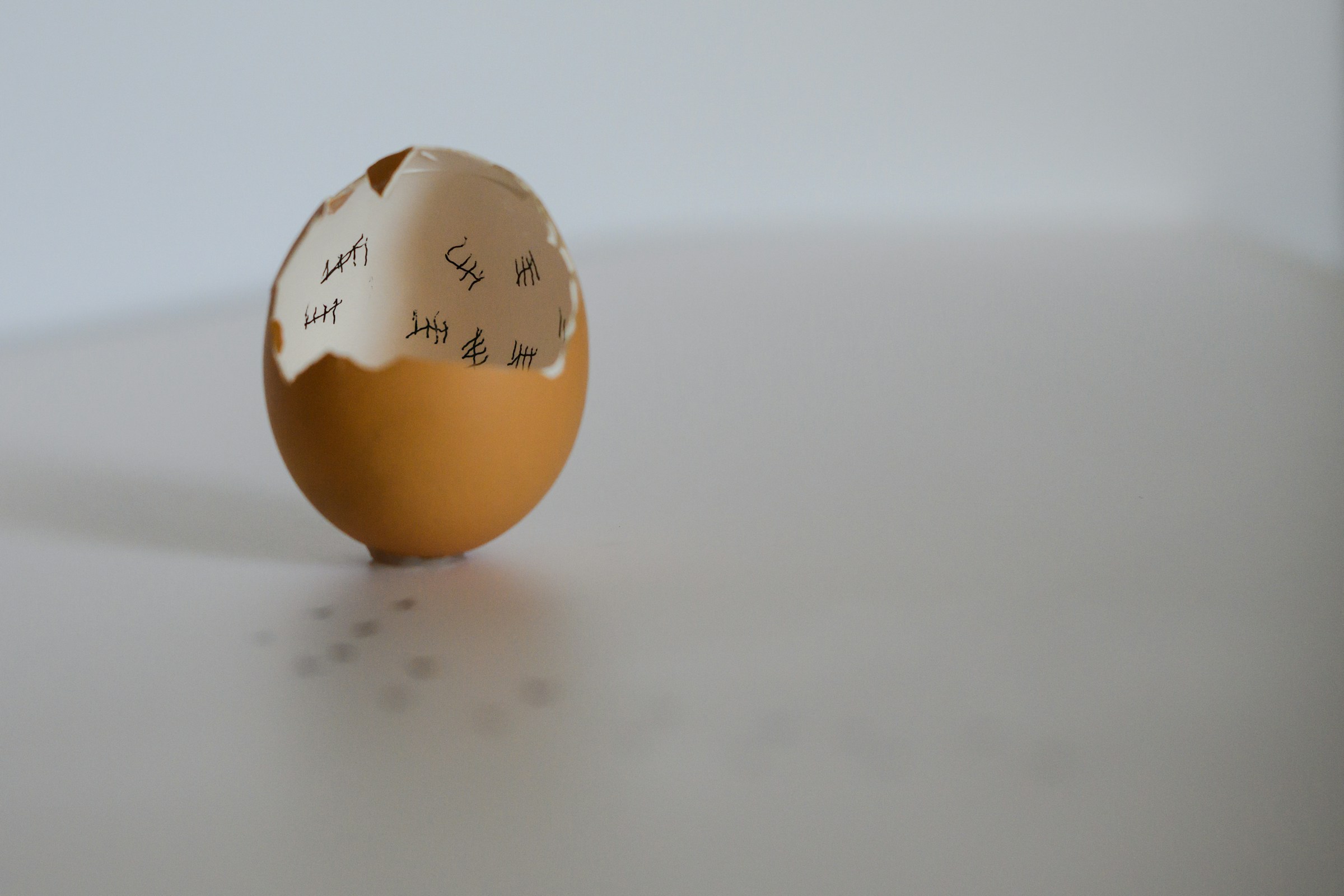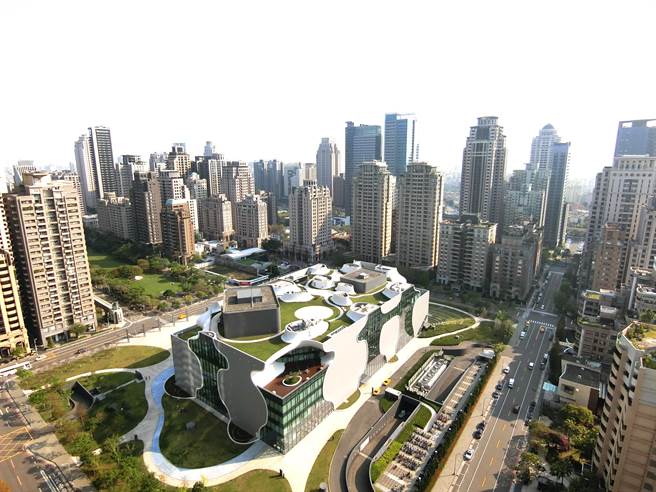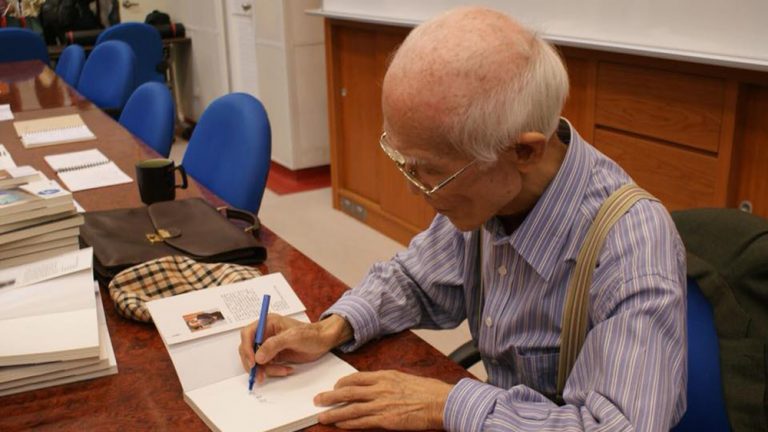◎文/衷曉煒
到這個題目,你可能會心生疑惑:一般我們都比較熟悉「破戒」──茹素的吃了葷,出家的犯了嗔,當官的貪了財,戀愛的劈了腿,戒菸的減肥的偷偷過了次癮等等。為什麼要調整順序,先「戒」再「破」了呢?
戒
去年12月,韓國當政者無來由的「戒」嚴,頗蹭了一陣子的新聞熱度。我們除了對戒嚴不陌生之外──臺灣歷經了38年又2個月,所謂「史上最長」的政治戒嚴;也該對華人日常文化裡的「戒」,耳熟能詳。
信手拈來就好幾個──戒鹽戒糖戒油,戒貪戒嗔戒癡。孔老夫子更在「君子三戒」裡面,將人一生的修養該戒的都一網打盡:少年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壯年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老了也還不輕鬆──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從頭到尾都要敬謹從事,時刻警醒;直到昇天之前,瞑目之際,再默想匆匆一生有無觸條犯戒,貽羞父母;然後才能感嘆「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安心溘然闔眼。
這樣的人生,好累喔。所以一有機會,凡人就想衝決網羅,突破世俗規範的圍城;所以許多望之儼然的大道德家大學問家,多多少少都有「例外」的時刻──「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大巧若拙、正心誠意的道德完人曾國藩,也會干犯「朋友妻不可戲」的天條,只能事後在日記裡自責「目屢邪視,真不是人,恥心喪盡……真禽獸矣!」印度的聖雄甘地,更是在年近八十歲時叫年輕貌美的女子與他同床,理由竟是:寒冷的冬夜裡需要別人體溫的幫忙,同時也要考驗自己能否抵擋誘惑,遵守禁慾誓言云云。明末清初的著名愛國文人黃道周的名句最具代表性──他在回應責備他冶遊的朋友時,辯說自己是:「目中有妓,心中無妓!」
我們這麼會戒、能戒,謳歌戒,但那些人生的終極考驗──愁、悶、苦,是戒得掉的嗎?
學校,就是個充滿戒的地方──既有校訓校規,自需訓導戒尺。比較特別的,還有「戒鞭」──直到本世紀初,少數新加坡的菁英學校,都還可以對學生施以鞭刑。
我有朋友親身目睹過這個算是濫觴於英國殖民時代的傳統「儀式」。整個過程完全「公開」、「文明」。首先,姑念學生尚未成年,所以鞭數大概都限制在二、三下;其次,准許學生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保護自己:能多穿幾條褲子都可以,反正除了棉被之外,墊多少東西在臀部是受刑者的自由。
施刑時也一定「公開」──全校集合,達到「示眾」的效果。所謂的鞭子,總有一公尺多長,下端是竹木,上端是硝製過的皮。負責揮鞭的,是學校裡特別受過講習訓練的老師。步驟是:施刑者先走向後方,然後轉身助跑四五步,最後一步躍起在半空中,同時右手「咻」地揮出第一鞭。第一下完畢之後,根據規定,老師還得問受刑者要不要喝水,身體還好嗎,可以繼續嗎等等。直到學生點頭了,這才重複之前的步驟,完成預定的鞭數。
還好臺灣學校並沒有沾染這個「優良傳統」。但,師生關係,可說是學校裏頭,最大最強,但也最無形無味,不言可喻的「戒」。
沒有比師生關係更具有辯證性的了。就老師們而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固然是教育這份職業的偉大願景,但為師者永遠要面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殘酷境遇:你的使命就是要讓現在這些看來稚嫩的少年少女們,將來比你更強。
談到師生關係,我們總想到有教無類、程門立雪等佳話。但除了道貌岸然的「傳道、授業、解惑」的儒家大師們外,還有沒有另一種師生的相處模式呢?
有的,答案在佛教裡──特別中國古代禪宗裡的師徒關係,其實更有人味,更能鮮活精準地體現應用在「長幼尊卑」界限漸泯的現代社會。
禪宗裡的師徒相處,「當頭棒喝」的故事大家都曉得,但這還不是最高境界──罵你一頓、踩你一腳,甚至作勢劈你一刀,讓你猛醒頓悟的故事也所在多有。讀著禪宗的公案,最令人低迴嚮往的,還是師徒間機鋒迭出的譬喻與啟發。
像馬祖道一,這個禪宗史上六祖惠能之後的關鍵人物。他的老師南嶽懷讓啟發他的經過堪稱經典:
一開始馬祖專修禪坐,是所謂的「面壁頭陀」。懷讓知道他是個「龍象之材」,便故意在他坐禪的地方「磨磚作鏡」,嘰嗄作響地讓馬祖受不了。當學生睜眼抗議時,老師劈頭丟來一個振聾發聵的命題:你說我磨磚不能成鏡,但你一味坐禪焉得成佛?
馬祖這下怔忪了:磚不能磨,禪又不能坐,那到底該怎麼成佛?懷讓便引導著著他往下想:「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還是打牛?」
當然打牛。能不能成材,關鍵在於自己。馬祖當下大悟:成不成佛,涅不涅槃,都在乎本心。
戒的精髓也在此。外在的束縛,繁雜的條規,看來不自由不人性沒道理的桎梏,目的都只在提醒受教者:心,修養,還沒好,火候未純,時候還沒到,功夫還沒學到家,再忍一下才能成材。自由奔放之中還是必須講求一點規律。真正的自由,其實來自於不間斷的自我要求與鍛鍊。砍柴挑水、青燈木魚式的苦修雖然不能一躋成佛,但至少「苦功」可以為將來的偉大奠定基礎。禪宗六祖惠能說的:「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不應成為泄沓拖延的藉口。
因為: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發慧。
健忘的我們常常需要一些有形的事物,提醒自己:戒的重要性。
比如戒指。凱倫‧白列森──寫出《遠離非洲》這部名作的作者,曾講過一個故事。大意是一位年幼的皇帝在長大到足以親政時,攝政大臣交給他一個戒指,並說:「我在這個戒指上刻下一句話,尊敬的陛下或許會覺得有用。當您勝利、凱旋、或是獲得榮耀的時刻,您都應該讀一讀它。」
戒指上只刻了五個字:「此亦有盡頭。」
破
戒的盡頭,就是破。年輕人一往無前的銳氣,是一個社會最寶貴的資產。不斷地衝撞戒條、顛覆既有、推陳出新,本來就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所以神話裡的大禹,才會從治水失敗的父親鯀的肚子裡「剖脅而出」;所以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里斯筆下的伊底帕斯,不自覺地成為弒父娶母的逆子,以完成他冥冥中「否定過去,迎向未來」的宿命。
我超愛以下的這個故事──這是「最會講故事的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轉述的。主角是一個對美國獨立戰爭有關紀念品患有戀物狂的男人──他聽說有個老太太有一件「在獨立戰爭時期穿過的洋裝」,便專程登門拜訪一睹為快。結果他看了之後激動不已,當場便將衣服拿到唇邊吻了一下。那位老太太大大不以為然:「陌生人,如果你喜歡親吻陳年舊物的話,你就親我的屁股好了,它比那一件舊衣服還老十六年!」
禪宗有個師生關係的故事更好。洞山良价二十一歲那一年去參拜南泉普願,身為當代大師的普願稱讚他:「這小子雖然年輕,但頗堪雕琢。」良价直接了當地吐槽:「和尚莫壓良為賤!」而良价的另一位老師雲巖過世之後,有人問他是不是肯定先師的道德佛法。良价說:「半肯半不肯」(意思是:我只肯定或贊成老師一部分的學問),那人不解:「為何不全肯?」他說:「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倘若對現有的知識與架構,戒律或限制,原則及教條,盲目地崇拜擁抱,不加思索地、不分生熟地一律接受,那麼老師費心教導啟發的價值在哪裡?年輕人的價值又在哪裡?
有戒,就有破;二者像是雙生子,不斷肯定否定,糾纏縈迴。那麼,破的時候,有甚麼竅門,要注意什麼呢?
今年春節前,有個「破」的大事:DeepSeek以超低的開發成本,在算力受限的情況下,找到了改變傳統訓練LLM大型語言模型的方式,推出全新的生成式AI模型,並完全開放原始碼給所有人使用,直接戳中資本主義操作獲利的模式,導致國際證券市場的大震盪。
無論這是一時的炒作或持續的存在,是過度的渲染還是真的開天闢地式的革命,這項新科技確定是個破除既有模式與概念的game changer──顛覆傳統遊戲規則的轉捩點。(按:有個有趣的聯想:這家公司中文的名字叫「深度求索」,似乎出自屈原的《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前中國的火星探測車,也被取名為「天問」一號。二千多年之後,《楚辭》又變為顯學了嗎?)
而想大破大立,改變既有典範、遊戲規則,一點也不容易。很少能像亞歷山大大帝那麼乾淨俐落、清楚明快──傳說古希臘的弗里吉亞國王戈迪安曾紮下一個複雜的繩結,沒人解得開。當時流傳的預言說:「誰能解開此結,便可統治天下。」
結果少年亞歷山大二話不說,拔劍就砍斷了這個「戈迪安繩結」。
很多時候,「破」必須植基於既有的「戒」──戒使得我們具備基本的修養,分析的眼光,進而能覷準改變的時機。正如 DeepSeek 是在前面眾多AI先行者包括OpenAI的成果上,進一步「蒸餾」精化,才達得到「破」天荒的成就。站在戒巨人的肩膀上,我們才看的見破戒之後,那遠方流奶與蜜的迦南之地。
此外,破的過程中,會有艱難險阻,冰塞雪滿的逆境,你常會有「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喟嘆。在眾多人事裡,堅定或頑固,短視或現實,同伴是井底之蛙還是培天大鵬,有時差異並不明顯。重要的是:別讓「藉口」當家,讓小小的自滿自足,阻障了你的前路。
第二次大戰,日、美之間的南太平洋瓜達康納爾戰役,便有個好例子。戰役是從1942年8月7日,打到1943年2月8日,日軍完全撤退為止──他們之中的二萬五千多人永遠留在了島上。撤退完成的2月9日,日軍「大本營」發布重大訊息,發明了一個新詞:
當天東京《朝日新聞》頭版大標題是:「南太平洋方面戰線確立了新的作戰基礎,我軍從瓜島、布納轉進」。
日方拒絕使用「撤退」,卻發明了「轉進」一詞,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因為民眾之前從未聽說過什麼瓜島,甚麼布納;怎麼,新聞報紙一直說大日本帝國打了這麼久的,看起來是打贏了的仗,現在又要「轉進」?
發明人陸軍省軍務局長佐藤賢了少將臨危受命,在次日用整整兩個小時向國會議員說明「轉進作戰」的偉大意義。這個「轉進」的藉口,宣傳成功了,而且持續成功了三年,然後日本,就輸了。
還有,若非必要,不用與同儕同工撕「破」臉──顧著大局,鬥而不「破」,有時會比「全盤顛覆,打倒重來」更好。
西元605年,阿拉伯半島上的宗教聖城麥加有件大事──當時伊斯蘭教尚未創立,麥加是眾多宗教神祇「共享」的聖域。
這件大事是:掌管麥加的古萊什氏族,要大破大立──重建存放神聖黑石的處所「卡巴」。這棟古老的建築物殘破不堪,且不久前因失火焚毀。
重建的過程還算順利,卡巴以一層層交疊的柚木和石頭重建。麥加各部族分工合作,每一族都要收集石頭,興建自己負責的那一部分結構。工程按計畫進行,最後只剩一件最重要的物品:安放那方據說是神賜的黑石。
麥加人開始爭論哪個部族該享有這份榮耀,應該由誰來安放黑石。大家拔刀相向,放話不惜流血。全城連續四天劍拔弩張,暴力衝突一觸即發。
在第五天,麥加人又聚集在新建的卡巴周圍爭辯,再度嘗試解決這個難題。這時,有個老人提出折衷方案──他建議在場的群眾:讓今天第一個進入聖殿的人決定。
先知穆罕默德是當日第一個走進聖殿大門的人──他當時還只是一個有著「老實人」外號的商人。大家說:「你是可靠的人,我們同意接受你的決定。」
拿到這個燙手山芋的穆罕默德,看著激動的群眾,思索怎麼樣才能在不破局、不傷感情、自己又不受連累的情況下,讓所有人都滿意。
最後,穆罕默德請人拿來一件披風。接著他把披風攤在地上,然後親手舉起黑石,置於披風中央,然後說:「每一族都派代表抓著披風的一角,大家一起把石頭抬起來。」這個公平的安排讓眾人點頭,大家合力把黑石抬高到適當高度,將石頭安放至定位,卡巴的改建於是大功告成。
旅行家艾瑞克‧紐比在《旅行家故事集》提到過以下這段話:「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我希望你們都又能戒,又能破;能戒中有破,能破中有戒;能戒得有始有終,又能破得淋漓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