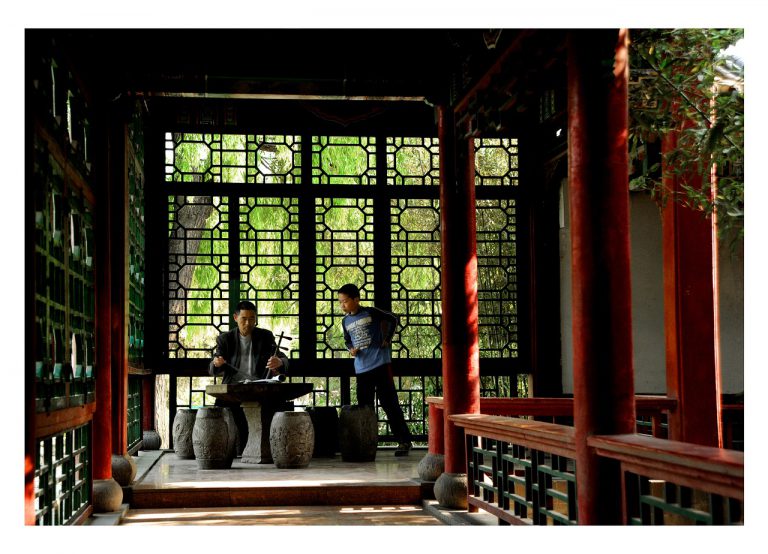啪——是鋼筆落在紙上的聲音。
啪搭、啪搭。
雨點打在陽台上,啪搭。
燈光有些眩目。很久以後,安杉才找回視線焦距,世界清晰起來,看見自己的腕部還靠在木桌上,手指虛握空氣,鋼筆循滾落的力道翻了幾圈,棕色墨水朝紙面暈開濃重的一筆,寫好的字全都一脈相承、連成一串。
他終於回過神來,意圖補救,被衛生紙擦過之後,墨水的痕跡看起來卻愈來愈糟了,最終,安杉決定把記事本收起來,裝作沒看到紙上的棕色大洞。
啪——他蓋上封面時,也發出這樣的聲音。
安杉持續發愣,思索剛剛想到的問題。上次吃蛋包飯是什麼時候呢?大概是到鄰居家作客的那天,想起蛋皮下的米粒反射迷人的番茄色光澤,口腔深處就忍不住分泌唾液。啪搭。他以為口水掉到桌上了,伸出袖子抹了抹,才發現原來只是自己的臆想。
他又翻開記事本,找到墨印底下的購物清單:雞蛋、番茄醬、奶油、米……思索一陣,他在後頭添上「筆記本」。安杉有個壞習慣,新買的本子用不了幾頁,就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丟在一旁,再也不用了。遺棄對他來說,大概是再簡單不過的事,眼睛眨也不眨,一切宛如過眼雲煙。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人呢?
啪搭、啪搭。窗外的雨好像有變大的跡象。在雨停之前,安杉還是打算暫且不出門了。他把鋼筆收進抽屜,往記事本前面翻,習慣記錄生活的人恐怕都有這種癖好吧——看到過去的日程陳列得整整齊齊,心裡便感到滿足,好像他的人生就此被放在俐落的方格間,生命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發展下去。
他往前翻,發現一週前記下的筆記,在備忘事項一旁的角落裡,似乎曾經寫了什麼,比兩個字多一點的寬度,應該是寫得太快太急,墨水還沒乾就蓋了起來,紙張深沉地化開幾朵烏雲。啪搭啪搭,他再度聽見雨滴的殘響。
安杉猛然闔上本子,轉過頭,對著因雨而潮濕黏膩的房間叫喚:「老薛。」
蜷縮在角落的生物動了起來,髒橘色的老貓翻開沉重的眼皮,皺著鼻子噴氣,像一瓣乾枯玫瑰,而這究竟屬於不悅、警戒還是困惑的表情,安杉還是看不出來。他不擅於跟貓共處一室,畢竟他從來不像會煮好吃蛋包飯的鄰居一樣懂得討貓歡心——像貓一樣,古怪、有時親人、若即若離的鄰居。安杉想給他更多形容詞,卻說不上來,彷彿他甚至不比一桌美味飯菜來得印象深刻。
喵。老薛囈語似地叫,然後,啪搭、啪搭。
安杉知道,這場雨還是沒有停下。
大雨夾帶著風吹過對面的窗簾,在黑色的布料留下更深的痕跡。望著從樹葉上滑落的透明水珠,安杉又開始想,焦洋他啊,到底去了哪裡呢?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他連名字都變得模糊不清了?
安杉剛搬進來時,還是盛夏,彼時他趴在車椅後背,看著藍色人影將紙箱從貨車卸下,塞進侷促的後車廂。十分鐘前,他們在路邊停下,搬家工人一邊擦汗,一邊哈腰道歉:「拍謝啦,山路太窄,真的不方便啦。」言下之意就是要把人棄屍山林。安杉扶起肌肉結實的工人大哥,內心五味雜陳,好不容易逃出讓他喘不過氣的都市生活,以為山上環境舒適宜人,與世隔絕前的最後一刻,他卻發現,自己還是一不小心,就被現代人心照不宣的小伎倆給繞了進去。
關上他的後車廂,一群人放下擦汗的毛巾,貨車時光倒流般仰長而去,安杉終於想起自己不會認路,也看不懂地圖,只好硬著頭皮,漫無目的地旋轉方向盤,過了很久,終於轉入一處村落。一路上非常安靜,沒有行人,只臥著幾隻被他驚動的母貓,喵嗚叫著,朝兩邊散開,就沒了蹤跡。
車輛駛進深處,他才古怪於這裡的寂靜無聲,沒一點蟲鳴鳥叫,卻很多貓,大多用一雙審視的眼神遠遠觀察,有些大著膽子在他視線範圍裡撩撥,又謹慎地逃開,髒灰色的、橘子色的、帶黑點的、虎斑紋的重影好幾次掠過車窗裡的視野。
安杉猜測,可能是這裡的野貓。這未免也太多了。
他不直接踩下煞車,以免引來居民,而是緩緩鬆開油門,車子在村落尾端的一排兩層公寓前徐徐停下。安杉瞇眼端詳,注意到這裡沒有門牌號碼。好奇怪啊,他小聲嘟囔。
安杉其實心虛得緊。本來找到的新房子不在這裡,可他又不是故意迷路的,他在原地掙扎許久,最終放下道德底線,安杉認了,要做個齷齪的房屋賊,就乾脆一點,反正這裡看來約略沒有住人。推開老舊的鐵門,立刻看到樓梯堆滿灰塵,他把手縮在衣服裡,避免碰到扶手上的髒汙,一往樓上走,便愈發覺得這棟房子實在不怎麼樣,戶形狹長、面積窄小、裝修簡陋、位置偏僻……除了還能住人,簡直一無是處。
他走下樓,還沒學會在塵埃間控制胸口起伏的頻率,一下子吸進太多灰塵,冷不防打了個噴嚏,靜止的樓梯間翻騰起來,他落荒而逃、三步併作兩步跳下樓梯,躲在車子一旁,祈禱無人撞見。
安杉這麼躲了一會,好像沒人聽見,便悄悄抱起紙箱,搖搖擺擺往房子裡走,大概是愈來愈少運動的緣故,沒多久氣喘吁吁,他又喪氣起來。盤算先睡車上,明天再繼續搬,對面公寓卻忽有響聲,他抖了一下,警覺地往上看。
唰——窗簾一下子拉了開來。
順著安杉的視線,少年從窗裡探出頭來,眼睛很亮,黑色髮絲乖順地蓋過眉毛、垂在耳邊,襯著銀色耳環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我還以為我聽錯了。」他低頭對上安杉的眼睛,「居然真的有人啊……你是誰?」
安杉想轉頭就跑,卻覺著無法動彈。等不到回應,少年索性翻過窗檯往下跳,腳步如貓,落地無聲,一片葉子都沒驚擾,安杉傻住了,直看著少年走到他的後車廂,步伐輕巧,毫不費力抬起好重的箱子。
「安杉。」他不小心回答,嗓音很低很啞。少年已經把紙箱抬上階梯,聽見安杉講話,他轉過頭,聲音穿透空氣中漂流的細小微粒而來,似乎也變得遙遠而悠長。
「噢……安先生。」他帶著笑意吟哦:「我叫焦洋。」
安杉心想,焦洋跟這裡很像,是個像貓一樣的人,聲音好細,就算壓著重物也腳步輕巧。他與他一起搬遷移居的重量,他沒開口說話,對方便安安靜靜一聲不吭,相對的公寓之間,彷彿存在一種靜定的平衡,無人破壞。安杉怕生,這種場合很少有不感到難以呼吸的時候,他卻難得自在,他想焦洋應該是個健談的人,但不做作、不搭話,說冷漠太過,更接近疏離一點,像繞過牆腳陰影的陽光,知道什麼叫保持距離。
他欣賞這種人與人分際的自覺,默默告訴自己,他並不討厭焦洋這個人,如果未來只要面對這樣的鄰居,那簡直是天大的好運啊。安杉向焦洋真心道謝,目送對方從門口離開。焦洋笑著擺了擺手,沒有回頭,只說:「這裡是九命鄉,歡迎哦。」
九命鄉。安杉默念,想,這真是好奇怪一個名字。
進房間後,安杉關上窗戶,注意到對面也拉上黑色的窗簾,心裡又踏實了很多。他站起來仔細打量新家,這房子確實狹窄,廚房衛浴臥室都小小一間,在角落並排,走出來,跨過門口玄關,就來到客廳,客廳比其他房間大得多,然而,他想不到自己有什麼理由用上能容得下這麼多人的空間。
安杉離開客廳,走進浴室,拉上淋浴間的門,水聲往耳膜注入今日份的喧囂。嘩啦嘩啦。水很熱,安杉久違地感受到溫暖,密布他疲憊不堪的軀幹與四肢。
安杉洗完澡後,躺在床上,抬頭就能望向窗外,但看不著海。記得來的時候經過海邊,所以九命鄉分明是個靠海的村莊,他開始想像晝夜交替之際,夕陽會被海底的鯨魚吞沒,月色將以星辰垂釣,慎重地花一晚上將它打撈上岸。
或許是等待太漫長,他恍恍惚惚看見有貓在房間裡,從窗口跳進跳出,一隻又一隻,把他的思緒踩得下沉,再踏深一腳,安杉就睡著了。
喀。澄白的蛋液含著金黃內裡,從蛋殼滑落,在滾滾冒泡的速食麵上濺起辣味水花。醒來時已經烈日當空,肚子咕嚕咕嚕叫,他睜著惺忪的睡眼,將蛋殼丟進垃圾桶,在鍋裡拌一拌,午餐就大功告成。
他端著熱氣騰騰的湯鍋回到折疊桌前,吸溜一口麵條,水氣凝結在鼻尖。其實安杉不太下廚,是外食黨,擔心食安品質的同時,又離不開餐廳和外送。先前試著自己下廚,結果當然是一場惡夢,最後,他還是不得不仰賴萬能的調理包,簡直拯救他無處覓食的人生。
他忍不住自嘆,這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失調症候群」,好發於他這種剛出社會幾年的、無依無靠的新鮮人,一旦離群索居,就沒了自給自足的能力。
「啊——嘶。」神遊太久,他被湯汁燙到,有點猝不及防,伸出舌頭哈氣讓溫度冷卻,刺痛的舌尖令他感到狼狽,這種時候——偏偏是這種時候,門口傳來聲響——叮咚。他手足無措,站起來時差點撞倒整張桌子,慌慌張張跑到門邊。
叮咚。又響了一聲。安杉趕在響第三聲前拉開門,想起打掃時他壓根沒擦過門鈴:「……焦洋?」他有些歉疚,好在對方仍然笑意盈盈。
「要來我家吃午飯嗎?」焦洋的語氣有些急切:「啊,你已經在吃了?」他嗅了嗅房間的香味,表情相當遺憾。
焦洋的殷勤友善,在安杉眼裡,宛如赤裸裸的討好。他架起防衛姿態,往門縫邊一湊,把屋裡的場景全擋在身後,「嗯,吃麵。」他輕聲說。
焦洋眼裡有光,聲音歡快極了:「真的?那你把麵一起帶過來,我好久沒吃麵了。」安杉被少年的厚臉皮嚇到了,看著對方臉上的期待,他只好妥協。
如果那時候拒絕會怎麼樣呢?此時憶起,安杉忽然慶幸自己就是個膽小懦弱不敢違逆別人意見的普通人,沒有焦洋的話,他根本不知道怎麼在這座幾乎只有貓的小鎮上活下去——就比如說現在,雨勢漸緩,他一手舉著傘,一手提著手提袋,走進小店時,他確信櫃檯上慵懶趴著的白波斯貓肯定瞪了滴水的傘緣一眼,立刻退出門外,把傘收好,貓店長咕嚕幾聲,安杉才像受到認可一樣回到店裡,肩膀放鬆地低垂下來。
這是焦洋教他的第一堂課:想在九命鄉過好日子,就要把這裡的貓當神膜拜供奉。那一天,焦洋做了蛋包飯,唯一一塊蛋皮放在安杉的盤子上,自己默默吃著平淡的番茄炒飯,口齒不清地咕噥:「你應該第一天就有看到吧,這裡有很多貓……很多。」
「牠們才是這裡的老大,不好相處,新來的小子不要隨便招惹,等會我帶你去轉轉,順便買點東西,你跟著我就好。」焦洋語重心長,一掌拍在安杉的肩膀上。他被對方古怪的言行嚇得無話可說,索性埋頭吃飯。焦洋是下了功夫的,安杉暗自讚嘆。少年雖然年輕,在廚藝方面卻顯然很有一手,蛋皮下的橘紅色米粒晶瑩剔透,番茄的酸甜口感在唇齒芬芳,還帶有淡淡的奶油香味,安杉很快就清盤了,滿足地舔了舔嘴角,注意到焦洋帶笑的眼神,又警戒地收回舌頭。
兩人離開公寓,安杉跟在焦洋背後,默默拉開三格階梯的距離,不近也不遠,剛剛好足夠暗中窺探,焦洋下樓時會弓起腳趾,全身的重量壓在小小的接觸點上,一聲不響地走著,窄小的樓道裡只剩下安杉的腳步聲,感覺破壞了無言的秩序,他只好跟著踮腳尖,試著不要發出聲音,牆上的聲控燈瞬間熄滅,在焦洋拉開鐵門時,又顛顛巍巍地亮起。
安杉問他:「我們等等要去的店在哪裡?是誰的店?」
焦洋輕聲竊笑,「你等等就知道了。」他說。
這算什麼跟什麼。安杉想,有些不耐煩,「那這裡的其他人呢?我是說,其他人住在什麼地方?」
焦洋停下腳步,沉默了很久,像是不知道該不該說:「……一個月前爺爺走了,從那之後,九命鄉只住著我一個人了。」
安杉啊了一聲,指尖捏緊家居服的下擺摩娑,「是你的爺爺嗎?」他直覺地發問,隨即立刻後悔,想給自己一個響亮的巴掌拍醒自己,這種問題根本問都不該問。
對方只是搖了搖頭,就繼續往前走,「是對我很照顧的爺爺。」他補充道:「阿茲海默症害他在生前的最後一段時光,都想不起我是誰了。」
「……抱歉。」聞言,安杉吶吶道歉。
焦洋的回應似在自言自語:「你別想太多,這種事總會發生的,我只是有點難過,我沒想到,陪他度過剩下時間的人會是我。」他轉過身,盯著老舊的公寓說:「爺爺一直有鼻炎,後來可能是吸收不好吧,變得單薄很多,體力愈來愈差……可是,沒有人來這裡看過他,直到最後也沒有。」
確實很難過。安杉心想,這次他沒有說出口。
焦洋領他繞了幾條路,最終轉進磚紅色屋簷下的小店,發出幽涼微光的冰櫃照亮三坪大的店面,出乎意料地,這裡該有的生活基本用品跟生鮮食材都有,唯獨收銀機後沒有店員,反而端坐一隻神色戒備的白色波斯貓,瞳孔緊緊追蹤兩人的一舉一動。
安杉狐疑地望向焦洋,但焦洋壓根沒把心思放在他身上,「是我啦。」少年清亮的尾音高高仰起,他從口袋掏出開罐器,揀了冰櫃裡的貓罐頭出來,打開放在櫃檯上,波斯貓跳上櫃檯,低頭湊近罐頭,長長的毛像淑女優雅的捲髮,湧動一層層波浪,令安杉想起海岸邊潮汐漲退,沙灘上留下或深或淺的水痕。
焦洋長吁口氣,「過來吧,你有什麼需要的就拿回去,店長同意了。」一面說,一面搜刮冰箱裡的罐頭和青菜,樣子熟門熟路,看來已經是老主顧了。
「這樣就行了?」安杉不可置信。
少年眨眨眼,說:「我講過了,想留下來,就要把這裡的貓當成上帝,這可不是玩笑話,是九命鄉生存指南。」
現在安杉知道了,人類對九命鄉的意義不過是過客、是過眼雲煙,在九命鄉,只有具數量優勢的族群有話語權,雖然貓不會說話只會叫。喵。安杉嘗試溝通,很快覺得自己就是個傻子,他怎麼能奢求另一物種能理解他用人類角度解讀覆誦的語言。
不像焦洋,安杉和貓處得不好,而日子久了,安杉也更加搞不懂九命鄉,一天到晚都安安靜靜,也沒有鳥叫聲。沿著這條巷子再往下走有一大片樹林,枝葉扶疏,深處躲著許多野貓。焦洋每天都去樹林一趟,安杉自認能理直氣壯跟上去餵貓,牠們卻很不待見他,每次靠近都逃得遠遠的,站在山坡上對他齜牙裂嘴,嚇得安杉也跟著倒退兩步。
「別鬧,當心被咬。」焦洋插足一人一貓氣氛緊張的對視,蹲下去哄貓歡心,俄羅斯藍貓被撫摸得饜足,尾巴跟耳朵都高高豎起,像得意昂昂的貴族,「牠特別怕人。」他說,安杉心有餘悸,回答,我還真看不出來。
安杉好奇地問過他,這裡的貓你都認得嗎?少年想了想,說,就算沒看過,那之後也會認熟的。畢竟他的生活裡幾乎只有貓嘛。安杉卻不知道,換作是自己的話,究竟能不能記住每一隻貓的樣子,也許焦洋給牠們做了特別的記號,少年卻說九命鄉的貓都沒有名字,「除了老薛以外嗎?」安杉好笑地問。
老薛又老又瘦,腐朽枯枝一樣單薄的軀幹長著稀稀疏疏的毛髮,因營養不良的關係而沒有光澤,形成某種實驗室裡會出現的詭譎的、黯淡的土橘色。
安杉某次拜訪焦洋的家時,對方正努力餵食那快要油盡燈枯的老貓,鬍鬚上沾黏肉泥的碎末,焦洋抽起衛生紙,擦淨老貓的嘴角,「原來你也養貓。」安杉說。他以為焦洋是野放主義,有點訝異。
焦洋並不同意,「他只是跟我住在一起。」
「這有什麼差別?」安杉又聽不懂了。
「我不能告訴你,自己慢慢悟。」焦洋不置可否,「這世界的規則倒也不是只有馴養與被馴養的關係。」
後來安杉才明白他的意思,老薛似乎在被發現之前,就轉移陣地來到他的屋子,變得更加瘦了,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偶爾醒來在房間裡繞幾個圈,又再度陷入睡眠,也不知道給牠準備的飼料到底吃了沒。
小王子的狐狸說馴養與被馴養是愛,但老薛既不是焦洋的老貓,更不是安杉的老貓。九命鄉沒有相互拉扯感性與理性的關係,他與牠的共通點只是找不到馴養的對象,同樣不想被馴養,卻也同樣需要焦洋。
需要。安杉琢磨用詞,不是想念、不是在乎、不是撕心裂肺,而是需要。需要這兩個字就很剛好。他們都有自己的規則在個人世界裡運轉。
他從小店回來,驚訝地發現老薛還醒著,順手打一顆蛋,去掉蛋黃,添上雞肉煎了,剁得細細碎碎,放在碗裡,端給老薛,「老薛、老薛……」安杉小聲喚道。
蒼老的橘貓受到驚嚇,警覺地瑟縮了一下,牠還認不得安杉,只記得自己的名字,無法理解為什麼這兩個音節會從不認識的人嘴中脫口而出。老薛的鼻子又抽動起來,安杉忽然覺得,也許牠是緊張了,所以朝著他噴氣,想趕走讓牠不安的人,但牠又為什麼要待在這裡呢,明明對老薛而言,相較於安杉的家,焦洋的家應該是他更熟悉、更值得稱之為家的地方啊。
焦洋還在的日子,安逸得很不現實。安杉有天停在靠窗的書桌前,發現散落滿桌滿地的樂譜,墨跡時不時在小節間大規模暈染,擴散成一大片安杉看不懂的旋律,「原來你還會寫歌。」他朝焦洋挑了挑眉。
焦洋在喉間低笑,發出奇怪的、像咳嗽一樣的聲音:「只說對一半,我寫歌、也唱歌。」
自己寫歌唱歌的人。安杉想起以前住的地方,旁邊的咖啡廳有歌手駐唱,總是帶著一把有歲月痕跡的木吉他,唱一些已經被人遺忘的歌。他遇見焦洋,少年住在沒有人的巷弄,任誰看來都是個奇怪的人,九命鄉也是個早就被現代社會忘記了的地方嗎?他在心裡把焦洋的家展開攤平看過一遍,沒有多餘的東西,屋子的主人有顆溫暖的心,把不夠寬敞的空間佈置成舒適簡潔的小窩,讓它充斥久居生活的足跡。
他想問焦洋,你也自甘於在時間中被淡化嗎?張了張嘴,最終什麼也沒說。焦洋看著他欲言又止的模樣,笑了,走到他旁邊撿起散落四處的樂譜,不經意道:「……你知道嗎,人跟貓其實是很像的。」
「不可能天生冷漠,久了才會習慣。畢竟,就連電視上耀眼的知名歌手都會感到寂寞,貓何嘗不會。」
因為焦洋懷中沉沉入睡的老貓,他倆都屏住呼吸。餘暉之中,少年的低喃帶有詠嘆調的悲傷,安杉沒看過他那副模樣,遂垂下眉毛,輕聲詢問:「你沒事吧?」
焦洋瞅了他一眼,忍不住噗哧出聲,「我只是隨口說說。」他調笑道,安杉就不服氣地紅了臉。他漸漸覺得,焦洋果然還是個小孩,挺平凡的,又不那麼普通,總是嘴角帶笑,古靈精怪,明媚卻憂鬱。
焦洋也從少年長成大人了。他滿十八歲那天,安杉興致很高,買了酒到對面拜訪,最終自己一個人醉得徹底。忘了當晚怎麼回家,只記著他渾身酒氣,從床上徐徐轉醒時,白日已然高懸空中,晃得他東倒西歪,險些一頭摔死在太燦爛的早晨中。
門鈴正巧響起。叮咚叮咚。焦洋送來一壺醒酒湯,「你連這個也能煮嗎?」他笑著問他,被掛著黑眼圈的少年斜了一眼,「先洗個澡,你有夠臭的。」他捏著鼻子把水壺塞進安杉手裡,走了,後腳跟在階梯上踩出結實的咚咚聲。
焦洋很久沒有踩著腳趾尖走路了。
如今安杉再怎麼努力回想,也想不出是從哪一個具體的時間點開始,焦洋的一舉一動有了點人味,他有年輕人該有的脾氣跟小孩心性,而不是好像無所不能的、如貓的、客套的、溫和的怪異鄰居。
他開始思考,他們身為彼此熟人甚至友人的可能性,或者是說,焦洋把自己當成朋友嗎?安杉不敢確定,確實有些關心是超出鄰居之間的敦親睦鄰的,然而,他更覺得,也不過是因為過去這些記憶,都只存在於他無聊時候的念想裡,那些善意的舉動、小小的玩笑被誇大疊加起來,就能證明他們曾經有過革命情誼了嗎?不管用什麼角度來看,邏輯都不合理。事實上,他們誰也沒為對方付出多少,兩人的互動像冬夜裡的火爐,點燃時炙熱,熄滅也無聲,不過需要時候各取所需。
可這樣又說不通了。鄰居理應不會一起看貓、縮在沙發上聽對方唱自作曲、有時聊天,即使兩人都沒話說了,相對無言,沉默也開心。安杉不敢承認,也不得不承認,焦洋已經占據他平凡一生中太大的份量,他們現在是同一艘船上的人了,安杉卻感到害怕,唯一意味著視線統一、相生相依、靈魂被互相切割組合成兩個新的個體。他很懦弱,他不想承擔互相依賴的後果,這種情況自始至終都是他始料未及的,之前是,現在也是。一直以來,一切都是。
此刻他在廚房烹調番茄醬汁,忽覺全身顫抖,連忙抱緊自己蜷縮成一團,像胎兒縮在羊水裡啼哭,又像遲來的青春期,他發起生長痛來,一瞬間連他都忘記了自己究竟身在何處。
他買了新的扣環式筆記本,能替換內頁那種,好像記憶是可被拆卸、錯置、不斷延展的,書寫的順序全都亂了,過去是未來的衍生,未來是現實的拼接。安杉做好蛋包飯,在潔淨光亮瓷盤上裝飾擺盤,回房脫下沾滿油煙的衣服,把寂寞的味道摺疊,在櫃子底層藏好,彷彿只要這樣,它們就不會滲透到生活當中。
會不會他也把自己藏了起來?安杉曾經以為貓的世界很小,小得只剩牠們打呼嚕的空間,但焦洋告訴他,貓也有不想自己待著的時候,如果牠願意讓你一起擠在牠窄小的空間,你可千萬不能拋下牠。
對於焦洋而言,老薛是這麼獨特的存在嗎?還是牠讓他想起了其他人呢。安杉忽然難受起來,神經末梢傳來未經稀釋的罪惡感,握不緊叉子,它向下墜落,落在地上發出脆弱的響聲。
若要追究當初到底是誰留下了誰,是他想遏止那令他恐懼的、過從甚密的情感連結,持續攀附、收束他與焦洋的關係,想離開的是他啊。晚秋時,低頭餵貓時,安杉把自己的打算告訴焦洋。他要走了,陪陪家人。少年柔和的雙眼遽然張大,凝結為一面冰層,「這樣很好,你是早該回去了。」焦洋低聲道,再後來的路上,他們一句話也沒說。隔天再見面,焦洋仍像平常一樣,沉穩自在。於是,安杉就忘記了,他或許該感到抱歉。
焦洋幫他收拾家裡,安安靜靜地把物品打包上車,像安杉初乍九命鄉時那樣。安杉發現他又開始踮著腳尖走路,差點大笑,但見著對方若有所思的表情,仰起的嘴角又在半路上僵住,有一種說不出口的違和感。
焦洋悄然無聲的步伐把時間踩在腳下,讓一切流逝得更快。關上車門,他才培養好離別前夕的心情,任由焦洋抓著自己的肩膀,雙眼明亮透澈,一字一句認真叮嚀。
「嘿,你答應我。不要告訴別人你來過這裡,不要想念這裡的一切,不要回來,如果可以,永遠離得遠遠的。我們過得很好,但九命鄉從來不是理想鄉,你明白吧。」
那時的焦洋,在害怕什麼呢?
離開之後,安杉總算想起少年語氣裡壓抑的顫抖,急急忙忙繞了回去。他大聲呼叫焦洋下樓,聲音傳遍整條小巷,眼熟的貓被他驚起,屈身躲進看不見的深處,卻再也沒有人,會從窗簾後方探出頭來,喉結上下滾動,發出唱歌似的招呼聲。
焦洋不見了。在這個隨便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引起注意的地方,焦洋理應是無處可藏的,少年的笑容卻交融在忽逝的光影當中,只剩下回憶時而遊蕩。
他的預感成為現實,在空無一人的路口盤踞成晃眼的墨水印,每當回憶悄然而至,安杉便會發現,自己似乎從未真正了解過焦洋和這個地方。思緒的餘溫喚起源自血液裡的不安,經過半個嚴冬的冰封,鋪滿灰塵的房間倒榻了,石塊水泥鋼筋深沉地壓在他身上,他動彈不得的同時,細小的粒子也侵入鼻腔、氣管、骨髓深處,嗆得安杉幾乎窒息。
焦洋曾經講過,寂寞是會吃人的,總有一天,都將順應人流的來去,變得不親旁人、不通人性,變得像貓一樣,是生而為人最悲哀的詛咒。安杉冷靜下來,慢慢想、沉默地想,似乎有些恍然,像紙頁末端染過棕色墨水,樂譜的尾奏呼之欲出。
蛋包飯還沒吃完,手中的盤子摔在地上碎成好多片,尖銳聲響刺穿思緒,他難耐地掙扎起來,從寬大的家居服裡逐漸脫落,翻滾到沙發之下,滾成一團好藐小的、連灰塵都沒能揚起的影子。
安杉想起,在好久以前的夢裡,也有一頭黑色的貓,躍過他的陽台,踩上對門的書桌,樂譜順勢散了一地。記得毛髮上頭點綴晶亮斑點,閃閃發光有如他睡前看見的星空,皎潔的月亮懸掛其上,左半邊尚未癒合,打撈不起遼闊大海裡的夕陽,自屋頂流淌下來,洩露滿地銀色的足跡。老薛在無聲的騷動間徐徐轉醒,彷彿察覺到情況有異,面朝窗外哀哀低吼,意圖縫補滑落指尖那古早的、沉重的——破碎的預言。
牠踮起腳尖,往前一步就浸入月光。九命鄉又靜了下來,一如安杉對這裡的第一印象,無聲無息、無憂無愁,沒有人,只剩下貓。
♦原作為39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高中短篇小說組 第一名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