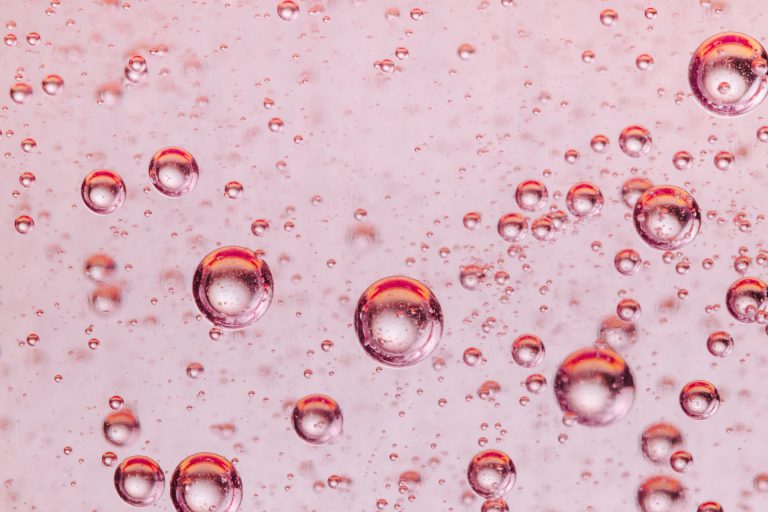情緒若能相通,必定是鬧哄哄的集市。人們甘願成為她的俘虜,愉悅時放浪形骸,悲傷時震耳欲聾。可惜看客終究是看客,打動他們的是情節的跌宕,不是呼天搶地的悲慟。
大巴車已經連續不停奔馳了七八小時,我看著窗外,陽光不算刺眼,天際萬里無雲,是極度澄澈的藍,仿佛什麼都一目了然。一旁路過的車不多不少,有的與我同行,有的向我的反方向飛掠而去,車窗裡有的人能看清神情,有的還未看清就駛走了。在車上睡了一覺的我托著下巴想,這些人自哪裡來,又要到何方去?
下車後遠遠就看到了一個極像父親的背影,腦海頓時一陣恍惚,耳廓盤旋著父母那場平靜而沉重的對話。「離婚吧。」「好。」「兒子怎麼辦?」「你要?」「算了,讓我弟照顧吧。」就這樣,我在三言兩語下被扔到了大半個中國外的地方,要跟一個素未謀面的「親人」朝夕相處。恰巧偷聽到這段對話的我那時想,不過是換個新的環境上學,一年後我便要成年,就當畢業旅行了,到時候不需監護人,恢復自由身,來去如風。
走近了,再一看,方才那一瞬間的熟悉影子蕩然無存。那個男人上身白背心,腰側又幾處耐人尋味的焦黃印字,下身大褲衩,一手插著腰,另一隻夾著根煙,頭向一側歪去,貼著肩膀上的手機,嘴裡吐著我很多我甚至都沒有聽過的污言穢語。我一步步移過去,有禮貌地說了句您好。那人猛地一回頭,看見我是誰後揮了下手,然後頭也不回地往前走,對著電話喊了一句:「行了接到了,以後沒事別來煩我!」我低著頭,一邊盯著自己的球鞋,小心翼翼不讓一顆泥土沾到鞋上,一邊亦步亦趨跟在那人噠噠噠的夾腳拖鞋後。
走了不知多久,那人停了下來。我抬起頭,眼前立著一座六層高的居民樓,建築墻身一塊一塊的焦黑霉斑,墻面開裂起皮,看著隨時要剝落下來砸人一身墻粉。最底下那層蹲著一群人,大致都跟那人差不多衣著,人手夾著一根煙,細細碎碎的吆喝聲傳來:「梅花三……過……王炸!」那人轉過身來,我終於見到他的全臉,跟父親的眉目的確有些相像,只是臉憔悴了點,牙黃了點,皺紋比年長幾歲的父親多了點。「小子,我是你叔,你爸不要你了,以後我們就住一起,這棟樓五樓左手邊第一個單位,平常不管飯。行了你自己上去吧。」我盯著他渾濁的眼珠子一個好字停在嘴邊,就見他把一串鑰匙往我手裡一拋,便急不及待地衝向那群人。
我無所謂地聳聳肩,自己慢悠悠走向居民樓,經過那群人時,那股濃得能起霧的煙差點沒把我嗆個半死。一拉開門,一直毛茸茸地東西從我腳邊竄了出來,我一開始還以為那是貓,上了樓梯後才慢慢從那過於細長的尾巴回過神來。在樓道裏跟各種小動物親密接觸後,我才進了「家」門,找到了屬於我的房間。房間裡一個衣櫃,一張床,一張桌子,飄著淡淡的霉味。木床腳的其中一根斷裂,被幾捆報紙墊著。掀開被子沒發現什麼生物,只揚起一片灰塵。我深呼一口氣,把背包放在被煙頭燙出洞的被單上,窸窸窣窣拿出這趟「旅程」為數不多的行李。一個頭戴耳機,一個高達模型,一袋內衣褲和幾件名牌外衣,幾瓶「時代大酒店」沐浴露,整體放在油漆幾乎掉光的鐵桌子上。
剛開始,每個人都對這個外來者很好奇,每次出門總能收穫一路上探究的目光,從上到下全身掃視,仿佛想把我整個人裡裡外外看透。我也不在乎,坦坦蕩蕩對上他們的視線。馬馬虎虎地湊合了一星期,每天到了凌晨就會被震耳欲聾的鼾聲吵醒,起來上廁所被滿屋子煙味和酒氣暈了腦袋,上了這裡唯一一所學校,開學以來完全沒跟同學說過話。日復一日,過了一個月,仍是如此。有時候走在路上我在毫無緣由地停下腳步,盯著地上出神,宛如在思考自己為何會在此處。偶爾會看見醉漢潑婦的互罵、拉扯、甚至打架,也只會瞥一眼,如看電影一樣看著這裡上映的一樁樁、一幕幕,心裡默默到一句:真可憐。可是,當你暗笑他活得不幸,他卻對你笑得朝氣蓬勃,笑你矯揉扭捏。這類爭執,三天兩頭就會撞上一回,很多時候主人公是同一個人,偶爾也會換換角色,輪番上演著對他們而言平凡不稀奇的人生。我融不進如今的生活,又回不去以往的日子。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沒有家,孤魂一樣在六合外遊走,靜靜注視著一切陌生,像一個孤獨的看客。
直到那天早上,我在睡夢中再次被吵醒,終於忍受不到想向那個收留我的陌生人大聲呼喊時,卻發現今天的噪音與往日有些不同。有些東西被摔在地上,不是瓷器,是人,我聽到拳打腳踢、拳拳到肉的聲音,聽到聲嘶力竭的呻吟和歇斯底里的求饒,聽到一群不認識的聲音一直悶聲威脅:「你還不還錢?不還把你腿打斷!」我大概知道了怎麼一回事,那人欠債,被仇家找上門了。我害怕極了,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像蟲子一樣捲縮在被窩裡,枕頭蒙著頭,豆大的汗珠從脖頸滾落,不敢發出任何一絲聲響,唯恐被發現。
我掩耳盜鈴般把自己藏起來,卻忘了居民樓薄薄的牆本就不隔音。樓上的人打開窗戶探頭探腦往下看,樓下的人極力仰著脖子往上看,隔壁的人緊緊關著門豎起耳朵,生怕錯過一點細節。圍觀者的覺得刺激快活,旁觀周圍的混亂和痛,讓他們得到娛樂。
生活在這個不知名小城的人,每天在犬牙交叉的幾條道路上走著,每個岔口最後都繞來繞去能回到原點,來來回回,幾十年來的人都重複著雷同的路,以至於不用昂首看路都能順著本能反反復復走到目的地。這些人的字典裡早就沒有了希望二字,或者向來不曾擁有過。只要有比自己活得更悲慘,比自己更絕望,便能其樂無窮,就是最可喜的樂趣。
我不知道今天這場鬧劇要如何收場,滿頭冷汗,一直藏在被子裡。過了很久,我終於聽到一些動靜,好像是那人掙扎著爬起來,出了門,然後再也沒回來,應該是自己去醫院了。樓下一直傳來若有若無的議論,一直等到晚上,我餓得實在撐不住了,把頭從被子伸出來,深深吸一口氣,從未覺得這口混著灰塵的濁氣是如此清新。外面漆黑一片,昏黃的街燈孤零零的矗立,很多商店都已關了門,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幾個行人。每每經過他們,餘光都會看見他們自以為悄悄地用手肘撞了撞同伴,朝我努起嘴唇,我覺得羞恥,每每躲開他們的意味深長的目光。之前的鼓譟忙亂被黑夜抹除,這一剎那我有種奇異和悲涼的感覺,如此嚇人可怖的喧囂,讓這麼多人為之尖叫躁動的事,僅僅數小時而已,一天都不到,全數消散殆盡。所有的一切都變成了家家戶戶亮著燈光的窗下的一段反復咀嚼的開胃小菜、下酒佳餚。
又過了很久,我下樓吃早餐,樓道裡迴蕩著噠噠噠的拖鞋聲。我打開門,準備迎接暖洋洋的陽光沐浴在我的白汗衫上。不過一抬頭,卻發現天空壓著濃濃的一層霧,觸目所及的世界一片白茫茫,看不清太陽的方位,也數不清有幾朵雲。一年?已經過了多少個一年了……在這裡待久了,跟所有人行著一樣的軌跡,走著相同的步伐,哪是想逃離就能逃開的。「喂!傻站著幹嘛?過來打牌啊,差一個人。」樓下蹲著的那群人突然叫住我。我抓了抓衣服,露出長期被汗浸透而染得微黃的領口,回道:「不用了,你們打吧。」
每個人一開始都袖手旁觀,或湊熱鬧或悲涼地看著這個小城裡的一切,本以為自己是這座城市的旁觀者,但生活於市井喧囂,誰又能真正游離於世界呢?踏進了泥潭,很多跟自己有關無關的事都糾纏在了一起,就算出來了鞋子上又怎麼可能不沾上泥?本只想做一朝看客,卻一不小心,入了戲,淪落成了戲中人。但是桌上的小玩意這些年始終從未鋪塵,一直提醒著我曾經的時光,每次當我沉淪戲中前告訴我與這座城生來就不同,帶著我避開泥濘地上的碎石和細溝。人在故事裡遊蕩,心在虛空中觀望。從看客的角度,讀著自己的故事。
♦原作為39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高中散文組 第一名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