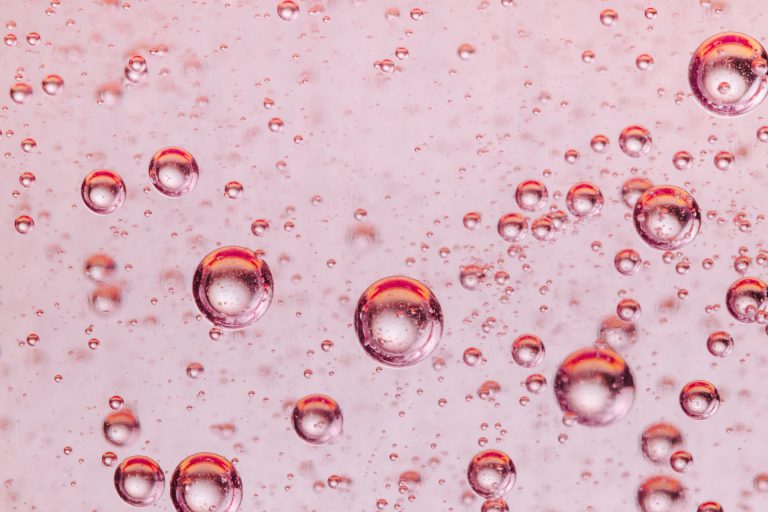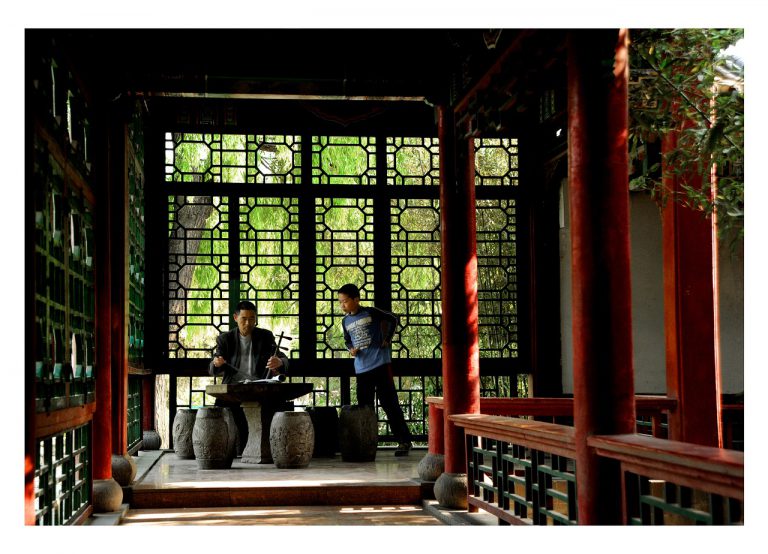那女人回來的時候,只穿著一件發黃的内衣和四角短褲。見伊葉盯著她,默不作聲朝她咪咪笑。那笑裡已經絲毫不見先前的兇狠與歇斯底里。
走廊的燈明明滅滅,三層的人知道她精神出了問題,只把她當作一個生了脚的塑料模特,閃爍的電燈有半是遮掩半是排外的驅趕。伊葉吸不得二手煙,索性把門關上眼不見爲净。她一回頭,發現娜娜剛點了根煙。她伸手奪過煙掐了。
娜娜擡眼睨她:「你在生氣什麽?」
伊葉說你明知故問,你明知道這樣的人回來不是被那些人渣玩死就是回去睡大街。
「你怎麽知道她就是回來賣的?搞不好人家只是回來拿東西。」
伊葉拗不過她,一會兒又打開門,女人剛好從她面前走過,這回好好穿上了衣服。究竟是有人嫌她穿得有礙市容(雖然C棟乃至這一區沒有整潔美觀可言)慷慨了一回,還是她真的和隔壁那家發生什麽,伊葉不得而知。
那女人之前和丈夫閙,隔著一樓都能聽見她喊你把我孩子賣了,懷裡還抱著一個,兩人扭打和砸東西能吵上一下午。兩天後幾個年輕氣盛的小子趁丈夫不在把她隨身帶著的布包燒了,艷色的衣物合著火光化作一堆嗆鼻的灰黑。後來她走了,據説是去睡公園,再也沒人見過她丈夫和另外兩個孩子了。她想起媽媽感嘆道:穆斯林女人不都是很保守的嗎。伊葉回答不了,因爲那時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個苦修女,除了逃避一概不知。她是最近才刻意關注這破旮旯的閑人瑣事的。伊葉自認還算文靜内斂,但和母親來到這裡后,她無時無刻不想著離家出走,或者直接一把火燒了這被判待拆遷十年卻比化石頑固的組屋。
這裡有條公式。住在這兒的除了窮,還都沒有好下場。伊葉現在住的這戶以前租給一個七十多歲的華人,死在醫院無人認領。後來換成馬來人印度人,很多很多人,多到沒有人記得他們什麽時候搬來,做什麽工作,哪年哪月和朋友一衝動去另一個城市闖蕩,或者因爲鬥毆販毒正吃著牢飯。每個人都是如此潦倒平庸,卻永遠上不了電視,成不了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奇觀條目之一。伊葉不知道住在這裡是否代表人生都會被蒙上一層社會邊緣的粉塵。搬進來第一天她戰戰兢兢躲在房間一晚上,後來發現根本沒人在意十八歲高中生的皮膚是不是和雜志封面一樣滑膩,也不會有人半夜把她連被窩搬走賣到國外。
後來把她從房間扯出來的正是這個坐在她對面的女人。一個隨心所欲的流氓,把她從十幾雙凝滯發亮的眼神中,從攤開向上來討香烟和零錢的被曬黑的手掌中拖出去。她朝著那些吊兒郎當或一本正經的年輕人們説了幾句話,語速很快,然後把伊葉拖進隔壁。伊葉這才知道女人就住在她旁邊。當然,她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從螞蟻窩挪到了狼窩,可無法否認,那一刻有莫名的安全感。伊葉並不清楚女人爲什麽在三層的少女中獨獨拉走她,不明白其他人對她厭惡又有點畏懼的眼神從何而來。那一刻她只覺得自己是一隻兔子,被狼蓋上了羊皮。
「你識字?那幫我寫封信,我不想打電話聽那老傢伙的聲音。」這是女人對伊葉的第一句話。於是她口述,伊葉照著寫。她第一次認真地聽C棟陌生人的聲音。女人應該是混血兒,有著混了方言的口音。皮膚是會被別人稱贊健康的顏色,與其説被曬黑,更像是天生的。她穿得和C棟大部分人一樣凑合隨意,頭上帶著天青色頭巾,有那麽一刻讓人感覺像吉普賽和嬉皮士的混合體。伊葉把她的渾話勉强整理出邏輯,用十足的應試風格寫得方方正正,字裡行間有想衝破格式的,屬於少年的强烈躁動。她已經好久沒有寫作業以外的東西了。
女人接過去也沒細讀,直接裝進信封。她似乎是這一刻才把眼前的伊葉當作真正的人看,但很快她的眼神也和那些彼此不熟悉的鄰里一樣,像是在看一只剛出生的老鼠崽。伊葉心想,她要是也討香烟,我就把信搶過來撕了。
「你怎麽來這兒的,多大了?」她漫不經心地問。伊葉卻渾身發冷,仿佛自己是待宰前有了智慧的雞。
「……我原本叫艾菲娜。這兒沒人這麽叫我,你和他們一樣隨便喊我娜娜就行。」那雙深褐的眼睛並不凌厲,只用她一貫的平靜直視她,就把她的虛張聲勢盡數撕開,露出搬來后最直白的恐懼不安。她的情緒漏水了,積聚在眼眶裡,於是頭低得更低了。
「伊葉。伊始的伊,樹葉的葉。」她很想回到三秒前把這副怯生生的語氣改掉。
娜娜皺眉打量她,似乎是感覺到她綳緊到幾乎斷裂的神經,大發慈悲地罷罷手趕她回去了。
伊葉後知後覺發現,娜娜那天的行爲近乎荒謬能說是一種保護。沒人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敲她家的門了。三層的人都挺怕她,更怕和她同住的那個據説有暴力傾向的獨臂男人。伊葉沒見過旁邊那家除了娜娜還有他人的蹤影。
晚飯時她問起娜娜。媽媽說你少摻和進去,和他們扯上關係遲早被人打死。
「可她就住我們旁邊啊,遲早會碰面的。」
媽媽想了想,「那樣的社會渣滓見不見都沒差。我們剛到這,聽你于叔的就行。」
伊葉敏感地發現那語氣下的蔑視,當下生出一股不服氣來。她想問我們爲什麽非要從老家搬來這種地方,成爲課本的「中下階層與貧窮家庭」之一,用橙色熒光筆劃重點綫,好像就能讓人對窮人、對那一排排像被攔腰砍斷的樹幹似的大樓有些橙黃色的溫暖印象。
那時的伊葉滿心不甘,哪怕泄露心思也要把一切問題寫在臉上。媽媽看著她,一字一句地說:「你是不是在怪我沒把你帶到更好的地方?因爲我很傻,把全部希望都寄到你爸身上,現在我要麽帶你回鄉下娘家,要麽在這裡裡熬到你成年。」
「因爲我們沒錢,你爸和我沒用。明白嗎?這裡魚龍混雜沒錯,可要是不和這幫爛人番仔一起,你媽就只能給你吃我的肉了!你到底會不會想!」
伊葉説不出一句話。像是驚雷後的寂靜,壓得湯匙都沉甸甸的。她第一次有了窒息般的沉重感,她大可以一走了之,做一個被環境汙染的壞女孩,可怨氣與不甘已經轉移到了那個曾經光鮮後來醜態百出的父親,轉移到那個及時幫了她們一把的所謂父親的朋友。她想到娜娜對她赤裸裸的審視,那審視的背後是C棟三層走廊衆多的脚步聲和吸氣聲,樓下機車發動的噪音,午後尖叫著推搡的小孩,小孩的媽媽正坐在門口上打呼嚕。種種生活的聲音匯聚在一起,又匯成娜娜問過她的:你怎麽來這兒的?
我是爲了逃出這裡而來的。她想,不甘與窒息感驟然消散。伊葉喝了幾口涼掉的湯,感覺滑入食道的其實是混了湯汁的酸水與嘔吐物。
她堵住了周遭所有的聲音,幾乎放蕩地讓腦袋充滿C棟三層的市儈好動,就像《女性癮者》的喬伊爲了欲望獻出童貞。只有那些畫面如膠水般的濁氣才能黏住她即將崩潰的情緒。伊葉、伊葉,她默念著自己的名字,好像第一次知曉它們的含義。她猛然從媽媽的幾句話模糊窺見生活的一部分,看清她曾堅信的由音樂、文學與水果蛋糕組成的青春只不過是一張剪貼而成的畫作。畫框後的掉漆漏水的墻壁,才是她現在的本質。她的青春是對另類藝術的刻奇。
伊葉來得不巧,剛開門就發現隔壁聚了好些人,嘈雜的聲音混著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她聽不懂,敲了娜娜家的門后就假裝是不經意碰到的,踮起脚尖朝内看。隔壁住的是一對老夫妻,妻子現在正靠在墻上抽煙,襯衫有洗得發皺的微笑圖案。一個看上去三十歲的男人,大概是他們的兒子,正哐當哐當地翻箱倒櫃,他的咒罵很刺耳,隱隱遮掩了站在大門前的印裔男人的話語。伊葉靠人們的表情隱約猜出些緣由。只見那個印裔在人群中推了一把,一個瘦小佝僂的老人踉蹌幾步走出人群,她才發現那個老人是如此矮小,仿佛周圍的人踏幾步都能把他踩死。
一隻手把她往一旁拉,伊葉下意識掙扎,臉頰感受到天青色頭巾拂過的觸感,又慢慢停下來。
「房東催債有什麽好看的。」娜娜笑道,把她帶進屋裡。
外面一陣騷動,之後是兒子一改先前蠻橫粗魯的咒駡向房東乞求的聲音。窮苦人啊、太辛苦了、離開這裡絕對活不下去的、行行好吧——周圍的眼神個個凝重,稍有差錯就會露出獠牙,這些借住的年輕人可比那兒子有用多了。一如既往,那收租的高大男人在喧鬧中先退一步離開。
「我不喜歡他們每天為錢為女人孩子爭吵的聲音。」她滿心的表達慾擠出這句話,再暗駡自己口不擇言。
「沒事,我也不喜歡。但要是連這些都聽不見,生活就是一潭死水。」娜娜掐滅煙頭,「你上次不是怕得快哭出來了,怎麽想到來找我。」
「因爲別人都怕你,你這裡最靜。」她不敢問你上次爲什麽要把我帶走。
話題又斷了。門外傳來隔壁那家兒子的咒駡,還撲上去想打那老人。妻子見狀也不抽了,一把抱住他不讓他挪步,看上去更像是母子扭打在一起。她們待在屋內聽著周圍的人勸架拉扯的聲音,等到聲音漸漸散了,娜娜才把伊葉帶到樓下。
她牽著伊葉的手繞過了樓梯附進趴著的幾條野狗,又在冰淇淋車買了兩支薄荷巧克力甜筒。這畫面實在太像是誘拐了。伊葉問:「你要把我賣了嗎?」
娜娜低低笑了起來,「就你這樣的能賣多少啊。原本想去工作的,但有你在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翹班,反正也不想幹了。」
「你不工作哪來的錢?」
「反正都要給男人的。你沒看見這裡那麽多女人嗎,有的是離婚被抛棄後強留下來的,有的是跟著男人搬過來的,能跟著男人來到這種地方佔空房,説明大家都知道男人是一群吃軟飯的。」
「那他們爲什麽這麽怕你男朋友?」伊葉想了一會,還是問了。
娜娜挑了挑眉,斟酌著說:「不好説,可能因爲他是‘做交易’的還很會打人吧。」
伊葉大概猜到了那句黑話的含義,默默地把它當作空氣一樣吸進去,甚至異常冷靜地想著有什麽特徵的人才算是癮君子,還是她周遭的人其實裡頭剝開都是被腐蝕過的骨架。
「你要是幸運就到二樓去,那裡人少,只有一個纏著你問東問西還什麽都要寫下來的怪人。但你其實根本不適合這裡。你躲在媽媽後面不敢出來的可憐樣,和這裡很不搭。」
天色灰暗,陰沉沉的云撒開一片。不久後就開始下雨,她們沒帶傘,只好繞進了便利店。隔著一條路的對面是已搬遷的麥當勞門店。她掏出口袋裡的手帕擦了擦伊葉半濕的頭髮,自己頭巾上的水滴落在報攤上的雜志。
「我以前還睡過這裡。」娜娜透著玻璃窗指向麥當勞門前的走廊。「你不知道睡在那上面有多硌人,有時候還會被人趕走。你還在上學吧?如果上學是爲了更好的人生,你怎麽來這兒呢?」
「我爸老打我媽,她受不了快離婚的時候,人跑了。我媽沒地方去,是我爸朋友介紹來的。姓于。」伊葉乾巴巴地概括。她想起小時候總被人調侃是大小姐。那時她才不到十六歲。之後的人生還沒過五分之一就畫上分割綫,庸俗的幻滅小説寫到高潮,主角被波及的親人成爲故事的犧牲品。她的父親原先是個商人,後來成了工人,他從所謂成功人士的光鮮到渾身透著股頹廢廉價的氣息,最終深深融入人群,找不着了。
「小朋友,話別説得那麽細。不過你説那朋友姓于啊,他專幹那種佔空房再變賣家具的活。小心你媽被他騙了。」
伊葉心想我媽被打的樣子你又沒見過,她報過警,打過婦女組電話,最後迫使她回去的居然是女兒。你不知道她是多麽渴望逃離我和那個家。在一個婦女部副部長都鼓勵縱容家暴的地方,你讓她逃還不如讓我逃來得實在。
見她不説話,娜娜有些無措地縮縮手指。她匆匆看了看天色,又把不情不愿地伊葉帶到隔壁走廊,將一把嶄新的紅色雨傘塞給她。
「你哪來的傘?」
「臨走前順的。第一次偷東西的感覺如何?」
伊葉不可置信地看著她,「分明是你拿的!」
「是啊,可是是爲你偷的,現在你也成共犯了。」娜娜緩緩笑了起來,最後就著雨聲放聲大笑,蹦跳著往柏油路跑。
伊葉忙撐開傘,可娜娜幾乎瘋癲地往回跑,踏上水坑濺起一灘水花,還無意間把一隻拖鞋卡在排水溝了。伊葉趁她擡手扔掉另一隻拖鞋的時候追上她,那感覺比體育考試還累人,「你發什麽瘋!」
「赤脚跳舞也不錯嘛,小孩。」回過頭對上伊葉的不解,「以後來這和我聊聊學校吧,女人孩子和錢確實挺無聊的。」
後來伊葉想起校園,只能想起校慶上彈鋼琴的林城。她是轉學生,到校的時間很凑巧地撞上表演,她被三三兩兩的女孩兒擠到了邊緣座位,卻離舞臺最近。伊葉對學校表演主張的那套傳達夢想能量的形式主義不感興趣。她喜歡上世紀的老音樂,如果將時髦與座位好壞做個比喻,坐在角落的她確實像個舊時代的殘黨。
林城彈得不好,至少沒有富家少爺的貴氣和藝術家的纖細,他看上去更像是被看好的老師臨時拖上場湊數的。但他傾注的情緒有令人詫異的力量感。臺下的聽衆都沒看見他的情緒和音樂交錯著,兩股相悖的力量互相遠離、糾纏最後撕裂開來,衍生出的兩條路徑可以隨意填上任何對矛盾的比喻和代稱,頗有早熟的躁動。但這種掙脫感和伊葉不搭,她只覺得對方比所有的富家少爺都來得驕縱。
「你分明是嫉妒他。」娜娜笑她小心眼,明明眼中的激動都藏不住。伊葉思考了很久那究竟是不是遇見同類的狂喜,還是被燈光迷惑的錯覺。後來她知道林城和每個心比天高的青年一樣,和她一樣,對理想空有盛大的抽象直覺,像青年抽第一根煙吐出一口隱秘的自我。林城和她交流不多,他一直游離在人群外追求脫離俗世的靜寂,在自修室的白色墻壁描繪十二星座的另一種畫法。他是個怪人,一個伊葉十六歲時會忍不住親吻的詩人胚胎。他和藝術家只差了一次苦難和涅槃。
「我搞不懂你們年輕人的夢想。」娜娜給她泡了杯速溶咖啡,躺下時頭巾遮住了沙發的龜裂。伊葉故作惱怒說道:「搞懂了你就不會和那些人廝混了。」她指的是門外那些來去匆匆,故意製造機車噪音的浮躁年輕人。娜娜搖搖頭,不願深入談及。
「我想看他會搞出什麽名堂,又忍不住想看他失敗後苦惱的樣子。」伊葉喝光咖啡,緩緩組織語言,「我根本做不了什麽。哪怕換了環境,説不定也是碌碌無爲。我想著有天帶媽媽離開,卻看都不敢看那個姓于的。」
「你媽最近壓力很大吧。」
「嗯,情緒很不穩定。姓于的來一趟,我都要擔心他偷我們東西,也不知道他跟我媽都説什麽亂七八糟的了。我其實更想讓他出門就被抓個現行。」
「輪到他被抓還遠著呢!比他年輕十歲老二十歲的應該都先去牢裡吃咖喱飯。不過,警察不會特地過來。坏坯子們全聚在一起不惹事還方便監督,多好!一有惹事的剛好過來一窩端了。」
「可畢竟是居民區啊,怎麽過了這麽多年還是個爛窩……遲早讓人給拆了。」
「說要拆,可也過十年了。誰讓你倒霉呢?淨是些黑與白説不清的事,還人少事小。你喊得多大聲大家都只當是小孩在鬧。你可能覺得這很悲慘,能逃出去好像比電影裡的伸張正義來得偉大。可我在這待了五年,不知看了多少次那群混賬吸嗨的樣子,還看過你媽那種女人被打著轟出去的慘狀。」
娜娜又笑了。她越來越不像那個平靜中冷漠的流氓,卻讓伊葉平白感到刺痛,「沒人幫得了的。阿葉,你只能自己生活。」
「別説了。」伊葉站起身,臨走前忍不住狠狠推了娜娜一把,感覺胸膛起伏得厲害。可娜娜經這麽一推,寬鬆襯衫下的皮膚露了幾秒,暗得駭人。伊葉連忙摁住她,跨坐在她身上用力扯開她的襯衫。那黑中帶紫的暗瞬間籠罩了伊葉最深處的陰影,漆黑色記憶連著沒開燈的封閉空間幾乎讓她窒息。伊葉全身的水都涌到眼眶,覺得自己餘下的軀體都死了。她聲音乾澀:「你最近不是一個人住嗎?」
「半夜回來的。你早睡死了。沒事,他也沒好到哪去。」娜娜疲憊地揉了揉太陽穴,伊葉想説你男人不是只有一隻手嗎,你怎麽不掐死他。你不是蝴蝶嗎,怎麽像隻蚊子飛蛾一樣任人打。你怎麽願意被這種人渣拴在這裡,你是不是也看出我媽被打過,你是不是也把我當那些不幸被欺負被占便宜甚至如我最初所想被賣掉的女孩。你幹嘛可憐我?
「阿葉。」娜娜的聲音很輕,泡沫一樣脆弱,很快就散了。
你他媽有病。她終是沒忍住駡了一句,匆匆回家了。
但沒想到有病的是她的舌頭,説什麽都一語成讖。于叔坐在飯桌旁,媽媽盛飯時瞥了她一眼。
「捨得回來了?我還以爲你認那女的當女兒了。」
于叔夾了塊肉,「小孩子叛逆期都這樣,別管她。」
「我要是不管她還當自己翅膀硬了!」
「算了,別爲了這種事生氣。阿葉,你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摻和,別讓你媽擔心。」于叔連忙打圓場,「你聽我一句勸,早點決定我可能會拿更多錢,有了錢就能離開了呀,左右也沒什麽好失去的。阿葉也成年了,大不了有我在嘛。」
「別叫我阿葉。」她惡狠狠地罵回去,決定坐實了所謂叛逆的罪。于叔的笑臉冷下來,當場就要發作,卻被一旁的媽媽打斷,「你決定吧,我信你。東西我等下給你。」
伊葉待不下去,將筷子重重放在桌上就走。她的媽媽是絕不愚蠢的,卻不明白那些過剩的信任從何而來。書上寫的諸如安慰劑與託付效應之類的東西,真的代表人能渴望依附他人到幾乎病態的地步嗎?她一時衝動去問了林城。林城的答案多半圍繞他最近沉迷的對宗教和哲學的思考,伊葉聽不懂,於是問他:「如果真有個高於我們的存在,卻不得不依靠低微的生物生存,那它其實是個騙子吧。」
林城沒聼懂她的暗示:「那可就是個荒誕的故事了。」
過了幾天伊葉放學,發現她媽媽坐在地上,眼神恍惚地盯了她一會兒,緩緩説道,「我知道你于叔要騙我,可我還是聽他的。我好像一直在等這一天。」
伊葉知道出事了。鍘刀終於落下來了。
「應該還剩一點我以前的嫁妝。但誰知道他什麽時候來討呢?他來了,我拒絕得了嗎?」
伊葉不用問。穿戴整齊的瘋女人走出三層樓道,抱著流浪貓的少年坐在撿來的塑料椅,壞女孩騎著機車出了小車禍,甚至赤脚踩在柏油路的娜娜,他們都如此普通,卻滑稽地滿心虔誠。組屋幾十年來沒往外傳出一絲動靜,只是向内長出透明的刺。她現在也明白那刺痛感背後,還有等待命運來臨後的如釋重負。
媽媽給了伊葉一個沉甸甸的盒子。「別打開,」她笑得輕鬆,「日子還長呢。」
伊葉伸手去拉她,拉不動,彷彿數十年的歲月斷了層,而她十幾年的人生還不足以兌換活著的通行證。她只是隻洋娃娃,正看著一個女人的哭與笑。伊葉想更往前一些。可她走不了,對方跨不過。媽媽拐了個彎,沒聲了。伊葉頭昏腦脹,等到終於能大口呼吸時,只看見卡其色窗簾微微晃動。她不知何時又回到自己的房間。
幾天後,她再次敲了娜娜家的門。
「死了?」
跑了。她堅稱。我逃走了,她也是。
「被請出去了吧。」娜娜沉默良久,給了她一根煙。
好像老大第一次給手下作案工具。伊葉定定看著它,接過去。
眼前霧蒙蒙的,像赫本或莫妮卡優雅吐煙根本只存在銀幕。伊葉被刺激得眼淚直流,忍不住咳嗽起來,但還是燃盡了整根煙,煙灰掉了滿地。
「成年快樂。」娜娜故作逗趣地揶揄道,隨後面色又變了。伊葉看不清,只記得娜娜緊緊抱住了她,力度勒得肩膀很難受。她哭得更大聲了。
畢業典禮倉促結束了。伊葉毫無波瀾地走出去,和幾個談得來的女孩寒暄幾句,快走出校門時碰到林城。
他略帶猶豫地繞開圍著他的同學,在她面前站得標準,語速卻很快:「之後應該很難見面了。憑你的才華一定會混得比我好。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感覺像戲劇才會發生的事。我總感覺我們之間某方面是共通的。可惜沒來得及深入瞭解,如果能早點認識就好了。」
伊葉想了想,發現彼此也沒深入聊過多少,聽説他最近得了國外的獎。她想説你不懂,不懂莫扎特光輝下的陰影還有薩列里,不懂藍色星空在C棟與圖書室看有截然不同的意境。她很努力達到標準的五育均衡分數綫多麽鄭重地印在那張紙,你卻非要看我縫縫補補依舊搖搖欲墜的自我追求。算了吧,她想,什麽樣的煩惱終歸是學生時代的了。
「如果你只存在上世紀的雜志封面,或許我會很愛你。」伊葉心裡閃過幾個曾無比閃爍的少年,從林佳樹閃到柏原崇,從西德巴雷特如鑽石的光輝閃到梅普爾索普的永遠純真。最後她想,算了吧,舊時代的殘黨還不至於飢渴到精神混亂見誰愛誰。
林城啞然失笑,朝她揮揮手走遠了。
伊葉目送一顆星星走上它的軌道,目送年少時有幸遇見的她心中的理想化身漸行漸遠。她走另一條路,低頭看見溝渠水和天空都平滑如鏡,像走在一條天青色的頭巾。
她回憶起臨行前娜娜把書包的東西倒出來,胡亂塞了幾件她認爲的必需品。娜娜認真地說:「走了就別回來了,反正我養不了你多久。」
她不以爲然,「確實會搬出去,但沒那麽快。我偶爾還會回來送東西給你的。咱互相養著對方唄。」末了警惕地補充:「你男人不會突然回來吧?」
娜娜聳聳肩,「誰知道在哪鬼混呢?」
離開媽媽後她和娜娜待了好幾個月,早就習慣娜娜做的參巴醬飄散的腥味和新來的少年時不時的敲門聲。C棟的喧鬧依舊煩人,但現在她巴不得屋内多一點動靜。她喜歡無謂的噪音在恐慌來臨前就切斷情緒入口的安心感。三層的人都知道娜娜養了個女學生。但之後就不是了,她長大了,她們早晚能一起逃出去。
她回來的時候,屋内很吵,幾個男人隨意地癱在客廳,各種東西碰撞得哐當作響,談話聲卻壓得很低。曾讓她安心的地方突然昏沉又頹廢,稍有不慎就會從陰影中把人拖進深處。她略過幾張還算眼熟的臉,驚恐地透過昏暗的光綫看見中間那人只有右手。見她在門口,靠在角落的娜娜臉色一變,連忙把她拖到樓梯口。
「爲什麽要回來?」
「你一直趕我走,我不回來看看才不正常吧?娜娜,他回來多久了?還有沒有打你?」伊葉心想這是碰上他們做交易的時候了,她下意識瞥向遠處馬路有沒有警車。她會被處理掉嗎?還是和娜娜一樣爲他們保守秘密,然後永遠在這庸俗發臭的地方沉淪?
娜娜沒回答她,朝屋裡做了個手勢,「賣白粉的,你懂吧?早跟你説不安全了。」
「你一定要在現場嗎?」伊葉焦急地抓住娜娜,「你找個機會逃出去好不好?」
「能走早走了。阿葉,你不是想逃嗎?機會來了呀。你別管我了,我走不了的。我還要忙著收尾善後呢!」
「你也和他們一樣嗎?」伊葉不死心。
「不一樣的。但是阿葉,你只能自己生活。」
「可是我想帶你走啊!娜娜,我們出去重新開始好不好?」
「你怎麽那麽傻呢!忘了初次見面你嚇哭了?你以爲他們爲什麽怕我?我就是個搶劫偷竊還强占別人房子的人渣啊!你何苦抓住我不放呢?」
「因爲我他媽想死,還想拖你一起,行了吧!」她不管不顧地大叫,出乎意料地發現自己比想象中更憤怒委屈。她心底升起一種曾經漠視、諷刺甚至司空見慣的情緒,像C棟大多數人的某一刻,心裡充滿無能爲力的憤怒。她原先以爲是C棟的空氣汙染了她,實際上她很早就變成了一臺憤怒的機器,將自己鎖在内部不停運轉,C棟的一切某種程度上與她一拍即合。娜娜,她幾乎在哀求:「你要是能出來,我們一起走好不好?」
獨臂的男人靜靜地停下腳步,伊葉不知道他聽到多少。他拖著娜娜往回走。伊葉追上去,幾個人上前做勢要打她,把她逼到樓梯口。她看見有人出來,下意識想求助,下一秒又看見那人漠然的視綫和曾經的自己如出一轍。娜娜掙扎著想過來推開圍著伊葉的男人們,可很快就被他們推搡著回屋。伊葉感覺那落下的鎖像是把她鎖在另一個世界。她又要被迫逃跑了。
「她那麽小,不會出去亂說吧。」稍微年輕的男人不滿地抱怨道。
「説了也沒用。警察哪有閑心天天來抓人。」旁邊的人漫不經心道,打開塑料袋遞給他。
「她要是回來就打一頓,保管乖乖聽話。」
「不會。」娜娜撫平衣服的皺褶,神色平靜,「她不會再回來了。」
可伊葉不聽話。她不報希望地打給關係還算密切的同學,出乎意料打通了。過幾天她又偷偷回到C棟。她找不着娜娜。那天的動靜大到估計挨了投訴,人都去避風頭了,三層靜得像是無人居住。她又到報攤前翻了地方報,沒有傳出什麽新聞。
伊葉一連等了七天,在C棟站到脚底酸痛。終於她想換個姿勢,剛一動就踉蹌幾步,接著步履奇異地輕快起來,仿佛連著地下錨點和她脚踝的鎖鏈斷了。她迷茫地感受這份輕鬆。四肢夥同心臟都在激動歡呼。這兒已沒甚意義了。她又逃跑了。
伊葉今年二十二嵗。開銷穩定,性格溫良,周末偶爾到咖啡館看書,看得很慢,多數時候在走神。
她回程時避免堵車換了一條路,繞過一棟棟組屋,凴本能踩了刹車。這是伊葉時隔四年第一次回來。她鼓起勇氣,閉著眼緊握扶手上三層。一睜眼,沒有還算熟悉的舊面孔,沒有犯囤積癖的佝僂老人和喝醉的中年婦女。走十一步,左邊第五間的大門改塗成紅褐色。沒有娜娜。她並不知道自己要找什麽。一個穿圍裙的女人給她開了門。伊葉眼尖看見客廳内兩個小孩在扯布條玩,下意識問道:「那條天青色的是頭巾吧,你還記得是誰給的嗎?」
女人警惕地擋在門前:「誰還記得呢?要麽死了沒人要,要麽跑了沒帶走。」
話音剛落,房間傳來一個男人的呼喚。女人僵了一下,把門關上了。那聲呼喚讓伊葉恍然回神,失望地發現三層和過去何其相似,卻沒感到曾經若有若無的刺痛感。C棟已經徹底將她排除出去了。故地重游,伊葉最初的困惑沒解開,竟感覺卸下了另一份重擔。
她去敲二層第一間的門。開門的屋主和她以前偶遇見到的變化不大。他已經六十多歲了。早就不記得某年某月被他要過電話的男男女女,也不記得伊葉了。不過,他可以為她翻翻聯絡簿。
老人戴上眼鏡,慢吞吞地翻頁。伊葉發現有幾個電話被橡皮磨得灰黑,看不清字跡,往後就再也沒動過了。她一邊希望娜娜的電話排得再後面些,又怕翻到最後也沒找着。老人頓了頓,看向伊葉,似乎想説些什麽,她忙凑上前,他指了指一行數字。伊葉終於拿到了娜娜的電話。她打過去,聽著響鈴又回到三層,剛剛敲過的那戶門後傳出模糊的言語。
伊葉漫無目的在C棟周邊亂晃,晃到商店街最後一間,上頭挂著的出租廣告邊角起了翹。走廊堆了些舊衣物,一個流浪的女人背靠著墻打盹。伊葉鬼使神差將這個女人和透過玻璃窗指著走廊的娜娜聯係在一起。女人狐疑地盯著她,伊葉別過頭,把這一設想和自己沒來由的衝動一同埋在身後C棟渾濁的空氣裡。
伊葉今年二十二嵗。生活平靜,工作穩定。現在她跌跌撞撞摔進駕駛座,放任自己痛哭失聲。所有混亂而不願回想的記憶碎片都如棉絮般將她塞得喘不過氣。年份、貝克特的戲劇、鋼琴錯音、金飾、永遠倨傲又溫柔的娜娜。
伊葉想留住它們任何一個,卻發現自己手指抽搐,視綫模糊。
♦原作為40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高中短篇小說組 第一名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