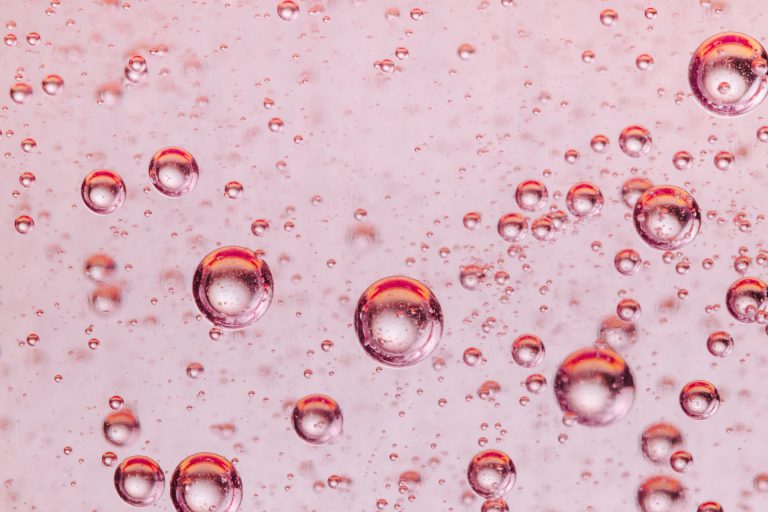♦原作為43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高中短篇小說組 第一名 張孔瑋 作品♦
篇名:受困
1
這條騎樓髒亂不堪。
除了被一整排違停機車占走大半以外,地上總散落幾個從爆滿的垃圾桶裡掉出來的瓶罐吸管衛生紙球;檳榔汁痕跡到處都是,不久前才有人被亂刀砍殺血灑滿地似的。流浪狗、貓、老鼠,遊民,都習慣在一家從未見它開過的店面前小便,甚至漸漸地在生鏽不堪的深藍色鐵捲門邊滋養出零散青苔,厚重的騷味用看的都聞得到。
裝滿各種米糧麵食等生活物資的粉色大塑膠袋的體積幾乎是他身高的一半,他提著這般笨重的巨物一步一步走在騎樓。中午不只熱,還悶,一點風都沒有,騎樓裡那各種骯髒物質混合形成的氣味就更濃稠更散不去;而他卻又不得不在疲累得大口喘氣的同時不間斷吸入這始終難以習慣的怪臭。額頭不斷滲出汗珠,凝聚起幾顆大的後就滑落到臉頰,下巴,或越過眉毛睫毛直接滲進眼中,又癢又痛但也只能忍住因為已經沒有手也沒有力氣可以處理。
他對於如何拒絕沿路上陌生人的協助早已十分熟練,只要聽到以「弟弟」或「小朋友」之類作為開頭的搭話,無需再待他們說完全句,「不用了謝謝」就能順暢地從嘴裡溜出來;雖然他有時還是會感到後悔。
又一次經過那位在捷運站出口前的斑馬線旁,捧著一紅色淺盤賣玉蘭花的代步車身障大哥,以及撐著陽傘蹲坐一旁,年齡與自己相差不大的應該是大哥的女兒。
走進捷運站後雖是涼快,但是更多關心和關注的視線投射過來時他只感受到更濃烈的羞恥;羞恥這個詞彙之於他的最直觀的認知便是來自這每學期數次拿物資的回家路。他努力加快腳步。
樓下大門也一樣有違停,要跨過至少兩台機車的坐墊才能按到電鈴,接著又得再爬五層樓因為這個家沒有電梯只有悶熱得要死人一般的樓梯間。他在爬樓梯時總是習慣恍神的而時常忘記自己爬到哪裡,但也只需要瞄一眼地上隨便一角落的髒汙便能知道此時所在。
「拿去廚房啊。」進門後他媽媽看著他把物資重重砸在自己面前。
「妳搬。」他跳上客廳那張連沙發都算不上的破爛大長條藤椅,又喬了許久遙控器的角度才打開電視。
他媽媽本想指責他的不配合態度,在看見他臉上的汗與幾乎溼透的運動服後作罷。塑膠袋沙沙地摩擦著磨石子地板從走廊一路被拖到廚房和其他各方來的物資一起堆在角落。
「獎學金的事情弄好了嗎?」他媽媽在廚房遠遠地問。
他無回話,臉漸漸臭成一團。她亦不再追問,只是從廚房端來一碗糊在一起的咖哩飯給他。
「怎麼又是咖哩飯?」他略有不耐煩。
「還有剩啊。」他媽媽說完便撥開門簾走進她房間。
他用湯匙挖起一口吃下去。即使咖哩與飯不會輕易變質,但一直在冰箱與電鍋裡進進出出造成的奇怪味道與口感也並非是吃不出來的。他好像明白了自己為何總在學校的午餐時間被老師誇讚是不挑食的乖小孩。
截斷動畫節目的廣告讓他試圖回想起自己上次吃到喜歡的麥當勞是什麼時候。向右瞥了眼媽媽房間可隱約看到媽媽又是老樣子地坐躺在床上邊看手機邊吃著廉價的零食餅乾,她習慣用這些東西充飢以撐到晚餐時間。
人把食物大口送進嘴裡咀嚼吞下的模樣總讓他無來由地產生憐憫。
*
自從開公車的爸爸因為一次未關妥車門讓一老人的腿被夾住且在路上拖行數公尺而賠了大筆錢還就此失業之後,他們家對金錢或說生存的執著簡直又更是到了種接近瘋狂的地步。他媽媽三五不時請他去問學校是否還有補助或獎學金之類可以申請,對於各方資助亦能拿就拿。這偶爾會反感到他,更多的是對那些總是要求別人七早八早跑個七遠八遠到某間聽都沒聽過的不知名宮廟或機構領個幾百塊大不了一兩千兩三千塊錢的「善心」產生厭惡,卻也早已習慣了去接受寫不完的感謝小卡和拍不完的照片、紅包味、一天到晚被討要的低收證明在學證明,還有那一袋袋對年齡剛過兩位數的小孩來說重得違反人性到一種不可思議程度的物資。
他會很好地完成這些事情。擅於寫出滿懷感恩與回饋社會之心的卡片再任由善心和鈔票擺布,任由巨大的塑膠袋反客為主地把自己提回家。小學四年級的他算得上過早掌握到敷衍了事的雛型和一點點卑微的知足心。
*
他爸爸今天回家後仍是慣性地煮了一包從隨便一個物資袋裡拿出來的乾拌麵在廚房餐桌上狼吞虎嚥果腹。他經過身穿發黃睡衣的爸爸身後,兩人還是沒有出現對話。他迫切期待著他能快點找到工作,比起賺錢,更是希望他可以重新像以前那樣在自己徹底睡著後才回到家,他覺得他們或許更適合錯開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尷尬地重疊在一起。
藏在看起來油油髒髒的瓦斯爐後面的蟑螂屋黏到了幾隻小蟑螂而置於餐桌邊的那個則留下一截完整的大蟑螂後腿。
*
即使現已六月他們家晚上睡覺還是不開冷氣,幾百塊的電費能省一點是一點。他早上醒來時總彷彿整個人要被電風扇風乾的汗水黏在硬梆梆的竹蓆床墊上。
*
失業讓他爸爸在家的時間多了,於是到客廳看電視的頻率也跟著提高。他爸爸常因為笑聲或發出的噪音太大而讓他媽媽出來罵人,有時則把其他大大小小的生活雜事一起糾纏進來升級成吵架或更嚴重的吵架。
他最近開始擔憂他們會離婚,思考在那之後是要跟著除了賺錢之外似乎什麼也不會的爸爸(雖然他目前失業),還是似乎什麼都會但就是不會賺錢的媽媽。不過仔細想想應該還是會選擇後者畢竟他知道他和他爸爸實在太過不熟。
客廳那張藤椅的其中一塊突然就在今天晚上被他爸爸坐得塌陷下去,媽媽破口大罵,爸爸順勢回擊回去,似乎就抓住這個機會把這段期間所有對彼此的不滿全部噴發出來,那是他看過他們兩人吵架得最嚴重的一次。
坑就一直留在那裡。
*
樓下的服飾商圈常有遊民帶著各式家當前來駐足停留,早上出門時他經過在地上熟睡的他們以及他們過夜時留下的一排紙箱城牆。不像龍山寺與艋舺公園到三水市場那一帶的遊民有著極具侵略性的刺鼻體味,且個性亦是較容易被火爆起來,這裡的就顯得相對溫和低調許多,衛生習慣也算良好。
店家遊民居民三者就在同一塊區域共存。遊民會在服飾店開門前就默默整理好東西離開,店家和居民不會驅趕遊民,彷彿是一個毫無交集亦互不打擾的生態關係,或者就單純是有一條誰也逾越不了的界線擋在彼此之間。
他在上放學路的各種地方遇到遊民時,有的伸手乞討,有的默默觀察別人走過,有的完全對外界一切不聞不問。他好奇這些人在成為遊民之前是什麼樣的,亦好奇怎麼樣會讓人變成遊民,或是更延伸地去好奇他爸爸會不會在哪個明天忽然又因為一場意外徹底破產,連現在的房子也再租不起然後三個人一下子就變成遊民,只能髒兮兮地睡在路邊等待別人施捨。
2
「欸你怎麼穿盜版的?」下課時間坐他隔壁的一個同學指著他的鞋子大聲笑道。
「什麼是盜版什麼是盜版?」旁邊其他同學也陸續湊過來。
「就是假貨啊!抄別人的!」
他看著鞋子困惑,這是約幾個月前他媽媽帶他去夜市攤販挑的,穿了這麼久,怎麼今天就突然變成了盜版。
「這才不是盜版。」他反駁道。
「怎麼不是盜版?人家三條線,你的鞋子有四條線欸!」
「就長得比較像而已啊!」他不免起了點情緒。
「不然你說你這雙是在哪裡買的?」
此時他身邊圍了四五左右個同學,他頓時感到一種以往都不曾經歷過的,全新的,要把胸口擠爆似的彆扭。他知道自己腳上這雙夜市來的鞋可能真的和某些品牌有著一點類似;但他不知道該如何以這些事實反駁回去,他不知道如何解釋,不知道如果把鞋子是夜市買的說出去是否會引來更多嘲笑。
「我穿什麼鞋子關你什麼事啊?」
別人怎樣關我們什麼事,我們怎樣關別人什麼事,他媽媽最善於使用這樣的語句組合,而這也是他認為目前能說出來的最難以回擊的一句話,儼然可以在自己腳邊劃出一大圈無法被超過的界線;然而那位同學卻直接哈哈大笑起來,「就是不敢承認自己穿盜版,心虛了才會講這種話啦。」說完,其他人也同樣被帶動著一起笑了。
他一下子愣住,不再開口直到上課鐘響。
之後一段日子的下課或體育課,每當他因為劇烈跑跳動而讓鞋帶鬆脫時,少數幾個同學便會有樣學樣地說盜版鞋就是這樣。他便漸漸地減少投入在遊戲以及球局中的運動幅度;同時開始克制不住地注意周遭同學的穿著,尤其鞋子,價格似乎都是動輒上千。和大多為四五百以內的便宜貨相比,自己渾身上下好像真的太窮酸了。
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認知到自己的生活是可隨意被他人越界並侵犯的。亦察覺到一種比起搬物資回家時被陌生人注視還更靠近自己一點的羞恥感。
*
「我想換新鞋。」他終於下定決心在某天回家後和他媽媽提出這個請求。
「啊這雙不是才剛買沒多久而已?」他媽媽的語氣如往常尖銳。
「就被同學笑啊。」
「笑什麼?」
「他們說這是盜版。」
「什麼盜版?」
他回答不出。
「以前的人在你這年紀都只能穿拖鞋或打赤腳上學欸。你看樓下那些遊民哪個穿得起這麼好的鞋?可以穿就很不錯了還計較這麼多。」他媽媽乘勝追擊一般:「不要隨便因為同學講什麼就吵要換鞋子,鞋子不用錢啊?」
對話不了了之。
他爸爸和他媽媽習慣在深夜交流自己這一整天遇到的事情,雖然大多時候是後者單向把自己的東西輸出給前者。他在床上半夢半醒間隱約聽見他們正談論鞋子這事。爸爸的態度基本和媽媽一樣,也沒有再多表示一些。
他開始嘗試對那個長久以來乖乖地知足地配合父母以及這個貧窮的家的自己產生一絲絲的憤恨。
*
一個請了兩周的假出國玩的同學在今天回來上課了。那陣子班上彷彿都以此為中心打轉似的,大家特別喜歡圍過去聽那位同學分享去歐洲玩的經歷然後瓜分那一大包從當地帶回來的零食。
他和那位同學的關係說不上太好。即使對歐洲一些事物多少也有點興趣,但看著那位同學邊聊邊不時伸手把袋子裡的東西隨意分給身邊的人,他便不自覺產生排斥,一模一樣的場景他早已經在各式慈善團體到艋舺公園發免費便當給遊民時看過無數次;而注意到每個和自己無話不聊的朋友們也都相繼拿了小零食回來,他更覺得自己像是一夕之間遭到背棄,就算朋友們熱情與他分享幾顆糖果或餅乾,他也全不接受。
「那你們家端午連假一樣會出去玩嗎?」「我爸媽說要帶我去宜蘭玩飛行傘。」「太酷了吧,那你呢?」「我們要去日本。」「好好喔,我出國還要等到暑假。」「要去哪?」「好像是去蒙古。」「真假?」「我也想去……」
他遠遠聽著那邊的對話。
*
「我們家端午連假要幹嘛?」他回家後猶豫許久才跑到媽媽房間門口問。
「拜拜啊,不然要幹嘛?」他媽媽跪在床上整理著帳單。
「沒有要出去玩喔?」
「什麼出去玩,家裡都要沒錢了還出去玩。」她抬起頭去看他。
「那暑假會嗎?」
「不知道。」他媽媽低下頭繼續整理帳單:「好了不要煩我。」
「我們家上次出去玩是什麼時候?」
「不記得了。」
「我們家沒有出過國嗎?」
「就跟你說沒錢了,是要出什麼國?一直問一直問煩不煩啊?」
「可是別人都……」
「那你去當別人家的小孩不會啊!」
他被媽媽的突然動怒和紙張瞬間飛散起的颯颯聲嚇得不知所措。
「別人家要怎樣關我們什麼事?要出去玩是不是?錢你出啊!還是你要排行程?什麼事都不會做還想著要出去玩?叫你去問還有沒有獎學金可以申請,拖多久了?還出去玩哩,去當流浪漢啦,每天都可以在外面到處乞討,多好玩啊?」
直到他離開去廁所時還能聽見他媽媽的碎念不停。
他在洗手台前呆呆地沖水,試著思考起這深不見底的不甘心,憤怒,與那無言以對又無從反駁及辯解的悶臭。
面對媽媽時好像無論從何處進攻都會讓自己變得傷痕累累而媽媽還是毫髮無傷,可他卻又從未能在媽媽的語句中得到被說服後改變想法的認同感,比較像是他先丟出了一些什麼但只是被媽媽原封不動甚至加油添醋地更用力地丟回來,砸得自己陷入一種彷彿連說話都成了邪惡的困境與劣勢後就無從再招架住媽媽接下來的一連串碎念,整個人中了毒後渾身僵硬似的。
為什麼別人可以各種去外縣市甚至出國玩,自己就得待在家;別人可以穿名牌的鞋子和好看的衣服,自己只能穿夜市的便宜貨。不知何時起這樣的不平衡迅速在他意識中明顯起來。他媽媽會說要知足,會說那你怎麼不去和非洲小孩比,不和路邊遊民比;可是一旦換成了學習狀況或成績之類情況卻又變得相反,不要老是和不如你的人比較,這樣不會進步。
那為什麼爸爸和媽媽就不需要進步然後還可以要求別人知足。
晚上他躺在床上黏黏地翻來滾去,強烈地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如果有個讓自己可以吃想吃的穿想穿的去想去的的這麼一個家,而不用活得如此窮酸,得到處提物資或領補助金回來,也不用為了省錢開不了冷氣而像現在這樣燥熱得難以入睡的話,那麼他定會表現得比現在更好更優秀。
他又聽見了廚房那傳來爸媽交談聲。
「連假後就會正式過去。」
「薪水呢?」
「就一樣是在十五號左右會發。」
「你這份工作最好做久一點,不要動不動就想著要辭職還什麼的。」
他爸爸沒有回話。
「再這樣搞下去家裡真的要沒錢了,做人不要那麼自私。」
「知道啦。」他爸爸微不悅地回。
「我才講幾句話而已你是在不耐煩什麼?」他媽媽又一次因為爸爸的態度而火爆起來:「你知道現在連帳單都快繳不出來了,小的又吵著要出去玩出去玩,叫你好好工作不要惹麻煩不要挑三揀四很困難嗎?」
「知道啦。」
「還有你不要每天都吃泡麵,吃這種東西又不運動身體遲早會壞掉。樓下四樓的都說你最近臉整個瘦下去了,自己注意一點。」
他努力地平躺在床上,心裡又不禁多了一抹罪惡和愧疚正與憤恨拉扯著。
*
雖說他爸爸總算找到正式工作,但或許是排班的緣故,讓他不再會很晚才回家。晚上九點十點左右即將入睡時他得一直聽見他爸爸在客廳看電視時發出的喃喃自語或是沉重的腳步聲拖鞋聲,這些瑣碎的吵雜令他煩躁不已,本來對爸爸不存在什麼討厭情緒的他現在甚至會刻意迴避兩人間本就稀少的互動跟接觸,像是在抗議家裡這個使他備感不自在與不快的他爸爸的存在。
不只是對他的爸爸,當他在端午連假的最後一天去了某一位好朋友家玩桌遊之後,他便更加不可逆地對他自己這個家感到同樣煩躁;因為別人家可以明亮整潔,不會有蟑螂壁虎,有沙發,柔軟舒服的床和好看的衣服,開整天的冷氣,要零用錢買零食時爸爸媽媽就直接一張千元鈔直直送到手上,根本不需要假掰地包在紅包袋或信封裡讓別人還要點頭致謝著拿。
他的表現和成績根本遠遠不如自己但為何自己擁有的卻根本遠遠不如他。
縱使會感到丟臉且厭煩各種補助與資助的繁瑣,他曾經也覺得自己的生活與別人無關,不過這條界線如今早已不再。
他不知道是別人先跨了進來還是他先跨了出去。
而現在他所怨恨的也不單只是食衣住行的一切的不如人,更是那或許早已註定的,簡直無從恨起的,只好在家裡用冷漠態度去回應的這份落差與不公平。反正除了擺一張臭臉和往外表達各種不滿之外他什麼都做不了。
*
今天是媽媽已經催促他好一段時間的某個獎學金申請的截止日期,他假裝自己忘了這回事,放學便把已經備齊且本該交給導師和教務處的資料隨手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然後再往裡面狠狠踩了一下。
這些錢到最後還不是一塊都不會給到自己,甚至當他過去對獎學金的處置有所意見時,他媽媽就會用「拿到錢不用回饋給家裡嗎?」把他指責成一個自私的小孩,一想到這裡他就極度不甘;而再想到其他人隨手拿到的零用錢都還比較多時,屈辱感又幾乎變成一個無底洞。
*
這天一個同學在最後一節課時抄他的數學作業卻不巧被導師逮住。明明自己已經多次提醒過他不要在上課時間抄以免被發現,但他不僅不聽,甚至在導師都還未開始追問之前就直接將所有同樣抄過作業的人一起拖了下水,現在那些人就在放學的走廊上排成一列罰站;由於他起初是因為被同學們拜託才會選擇將作業借出去,所以導師只是單方面念個幾句便放了他。
他背上書包快步走出教室,其他人就這麼望著。
原以為那些本就不愛讀書的同學在那天之後還是會持續找他借作業,然而並沒有,他們應付作業的方法只是從抄變成隨便寫寫敷衍過去罷了,班上所有人都沒事一樣地依然過得十分正常且快樂;反倒只有他一人因此陷入一股彷彿有什麼被消失或被剝奪了的空虛裡頭。
在最一開始他確實是不太願意把作業給別人的,憑什麼可以用抄的來不勞而獲得到自己一步一步算出的答案;但時間一久,看著大家圍成一團匆忙地抄抄寫寫時,他便感到自己正在被肯定,也從中得到滿足感和存在感,就像看到螞蟻千辛萬苦而只是為了把自己隨手掉到地上的餅乾屑搬走一樣。
他似乎完全理解了為何那些富人或廟宇或機構會想把錢捐出來,原來施捨是能帶來快感的,長久以來作為被施捨者的他在一眾同儕之中成為了施捨者,這尤其令他著迷。他之後總是爽快借出作業,也很快懂得透過這種穩定且頻繁的由上而下的給予關係從同學們身上獲得他需要的,例如平時總因跟不上有關物質層面的話題而間接低落於他人的社交機會,少許的利益,甚至友情。
不過只因為那個同學以為不會被發現的自作聰明還有導師的正義正確之舉,他活生生失去了這頗有分量的正向回饋的來源。他再也沒有籌碼去抗衡那藏於大腦某處因意識到了不平衡和不公平的存在而生的匱乏感。好像回到了一個早已變得不一樣的原點。
3
「為什麼這次數學考這麼爛?」他媽媽拿著他那張需要給家長簽名的八十五分的數學期末考考卷。
他沉默良久仍給不出一個答案。
「講話啊?考這種爛分數你好意思啊?」
「不然應該要幾分……」他小聲回。
「講那什麼話啊?你以前的分數你自己不知道嗎?」
「那是以前,現在又不一樣,」他從總是感到憤恨的那個自己那裡借來了一點反駁的本事:「而且明明就有很多人都考得比我爛。」
「還敢頂嘴!」他媽媽發出幾近尖叫的大吼:「這麼喜歡比爛是不是?就這麼喜歡跟別人比爛是不是!」
「那妳就不能知足一點是不是!」
他第一個瞬間是驚訝於自己竟能講出這樣強大又幾乎無懈可擊的話,甚至因此產生一點得意感。
他媽媽錯愕地瞪著他數秒,隨後才像是回過神來一樣讓臉上有了憤怒至微微脹紅的表情。她用盡雙臂的力量抓住考卷,握緊的拳頭讓紙張表面炸出難以回復的深刻皺褶,接著蹦的一聲,考卷被扯成兩半,然後再一陣手忙腳亂將之撕成更爛更碎的不規則廢紙屑。他從未想過她會反應得如此劇烈,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應對當前這樣狀況。
「出去。」他媽媽平定得詭異地說。
他於是照做,撥開門簾出去,回到自己房間。
雖然他一方面在想著該如何向老師解釋考卷被撕爛一事,一方面卻也慶幸他媽媽雖然生氣但難得地選擇了一個可以讓雙方都好好冷靜下來的做法;還有另個方面是他覺得自己剛才說得真好,把一個人曾經講過的話原封不動送回去是多麼具有說服力,他全然認為他終於贏過了她。
不過不久後他媽媽就從隔壁房間走了過來。
「欸,你這陣子的態度真的是很糟糕你知道嗎?每天回家就是一副臭臉,是想怎樣?我欠你是不是?」
他故作鎮定躺在床上玩那台廉價又時常當機的劣質平板電腦。
「有沒有聽見我講話!」他媽媽又一次大吼起來。但他嗯了幾聲之後也沒再多做回應,他清楚知道在這種時候回話是絕對不會有好下場,但不回話通常也不會有好下場,無解,他始終不善於應付他媽媽的情緒,應付這個家。
他媽媽不屈不撓地繼續在他房間門口碎念:
「你看捷運站前面那個小女生,年紀跟你差不多,人家已經會幫忙他爸爸賣玉蘭花了欸,每天放學都在大太陽底下曬,人家的爸爸甚至是殘障欸,你都不知道你已經多幸福了,不用工作也不用幫忙家裡,只要乖乖考試讀書上學,結果呢?現在盯一下你的分數就在那邊發脾氣,然後整天吵著要出去玩,要換鞋子要買衣服,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還在學校把作業偷偷給同學抄欸,搞這種偷雞摸狗的事情最會,然後叫你申請個獎學金還可以給我忘記。所以呢?你說分數要知足的話,那大家就都不用進步啦,這是不一樣的觀念你知道嗎,根本就搞不懂還敢嘴硬……」
「夠了沒啊?」他放下平板從床上跳起:「到底夠了沒啊?」
「你那是什麼口氣?我都沒生氣了你生什麼氣!」
「妳到底想要我怎樣?妳到底想要我怎樣?妳到底想要我怎樣!」他終於忍受不住也再不想繼續忍受他媽媽的陰陽怪氣。
他氣得噴出眼淚炸出鼻涕,發狂般地搥打床墊,老舊彈簧床發出一陣一陣嘰拐嘰拐的像是要散掉的聲音:「憑什麼啊!是我的問題嗎?是我的錯嗎?是我的錯嗎!別人有的東西我就不能有,別人可以出去玩就我不行,妳就只會知足知足,啊別人考不到的分數我就要考得到!我已經很知足了最不知足的就是妳!妳去叫遊民考九十分啊!去叫賣玉蘭花的那個考滿分啊!去啊啊啊!」
「現在要造反了是不是!只會叫叫叫,抱怨出一張嘴最會啦,要買東西要出去玩有本事錢你自己去賺不會啊,生你養你給你吃給你住已經很給你面子了,不然我現在把你轟出去,你就去路邊乞討嘛!一個晚上你都活不過,還不是要哭著回來求我讓你進去,莫名其妙,浪費錢養你還得在這裡受你的氣。」
書桌被他的拳頭砸得咚咚響,所有物品隨著震動跳起悽慘的舞步;放在地上的書包已經狼狽地與其他課本和學習單和資料夾一起被踢飛在角落。
「那就不要養啊!不要生啊!妳什麼都給不了啊什麼都給不了啊!要不是別人看我們窮給我們錢給我們東西要不然我們全家都一起餓死算了!餓死!大家都去死!妳就哭著去求別人可憐我們啊幹!」
「你再講一次?再講一次!你剛才講那什麼東西有種再講一次!」
「幹恁娘!幹!我幹恁娘機掰!」尚未開始變聲的喉嚨幾乎要喊到沙啞。
「你他媽的……」他媽媽作勢要衝進來。
他於是向房間門口撲了過去,用盡全身力氣抵住門將他媽媽卡在外面,他的兩隻腳頂著身後的衣櫃借力,雙方就這麼僵持不下,而他媽媽仍繼續碎念著與方才無異多少的話語,他則用一次次放聲的尖叫在她的任何一句話成形之前將其直接打斷:
教育失敗啊啊啊啊啊;不孝子啊啊啊啊;滾出這個家啊啊啊……
因為叫累了便失了點力氣,他媽媽的手從越來越開的門縫滑了進來,他見狀隨即更使勁地推門,甚至毆打那隻手臂;當他媽媽痛得不得不退回去時,門便爆炸似地關上了。他快速按住門把並上鎖,再轉過身讓整個背部徹底抵住貼緊門板,努力無視後面來自他媽媽的敲打和罵聲。
「好啊,都不要出來啊,你就給我一輩子不要出來好了!」
這個家總算回歸平靜時天色已漸漸地黑。
他仍然坐在門後,情緒流乾地陷入不自知的呆滯,全身似乎都在發痛著。帶髒字地大吼了一頓之後他卻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因此被宣洩了,更不覺得他會只因為經過這次吵架就不再憎惡他媽媽,他爸爸,他的家,還有別人比他擁有得不只更多的。
應該是好久好久以後他嗅到廚房那端隱隱飄來飯菜香氣。剛回來的他爸爸敲了敲房門,他不知如何應,所以不應。他媽媽語氣很差地叫他爸爸放棄;他的臉又一次像毛巾那樣扭成一團並擰出了最後一點眼淚。
他受困在這裡。
♦原作為43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高中短篇小說組 第一名 張孔瑋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