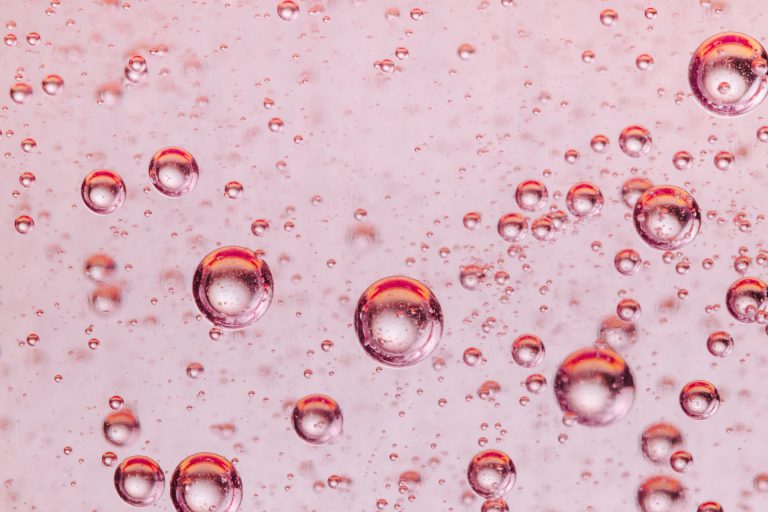「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红瘦?」
清晨早起,看著昨夜大雨打落滿地海棠碎瓣,使我憶起李清照的小詞。雨後的空氣沁著一種別樣的蕭索冷清,海棠鮮艷的顏色看起來格外刺眼——那是爸爸生前養的。做事不心細的他,對家庭亦缺乏責任感,唯有在照顧海棠花時,才會很認真。所以這盆海棠,不僅茂盛,更是豔麗。
*****
小時後,母親、父親與我共同住在一間老舊的鐵皮屋,昏黃的光線,總是帶著溫暖的和諧。斑駁老舊油漆牆卻比現今的堅固,更容易承載一家子的幸福。直到有天家裡來了幾個不速之客,年幼的我並不知道槍枝與法律代表著什麼,但我知道是冰冷的,或許出於血緣,或許出於愛,他們帶走爸爸的時候,我哭了。
父親因為幫人偷渡而被抓,而我們家也因為爸爸做擔保人而負債累累。隨著時間的流逝,名為大腦的程式,只備份了沒有爸爸的委屈和對爸爸離開的憤怒,而屬於我們之間的親情羈絆,也被研磨成僅剩最初的血緣而已。
爸爸出獄後從沒和我們連繫,直到我五年級的時候,他卻突然地出現。記得他回家那天,我望著他高大的身影,鋪陳滿陌生的氣味,我滿心是尖銳的猜疑、不諒解,但對「爸爸」的渴望卻矛盾地使我想親近他。我找了千萬個理由同情他,卻同時拒斥他的回歸。我不想原諒他。
爸爸回家的第一個冬天,某個週末,大雨,我跟著游泳隊在訓練,即便是室內溫水泳池,水溫依然低的嚇人,我必須奮力在水裡讓四肢活動起來,才有對抗寒冷的熱能。游著游著,教練把我叫上岸,說我爸爸在門口。我緊繃著一張臉,沉默地走到父親面前,離水的我像一隻瀕死的魚,因氣溫而瑟縮發抖,心裡充滿對父親無端到我訓練場地的憤懣。
「你有事嗎?」我不冷不温,彷彿身前這個因大雨而一臉狼狽的男人與我絲毫無關。
「外面下大雨了,怕你冷,這錢你拿著。」他手中的一百塊紙鈔,混著雨水與手汗,早已揉皺而形體難辨。
「喔。」我不耐煩地看著他。
「我至少……還是你爸爸。」他的聲音如同細雨滑過,混在大雨聲中,模糊,幾乎無從辨起。
「你不是我爸爸。」
寂靜就像堅固的牢籠,凍結此刻我們父女周遭。我看著爸爸流下了眼淚,獨自一人往雨裡走去。我想追出去,但我又倔強地覺得,我要他的道歉。道歉什麼?我也不清楚,為他的缺席道歉嗎?為我的不幸福道歉?還是為所有的一切道歉?
看起來我似乎成為更需要給爸爸道歉的人。
訓練結束後,回了家,後悔的情緒又湧上。他在雨中的背影一直揮之不去。進了家門,爸爸卻衝著我笑了一下。
我卻又想起他離開時的情況,為什麼他總是如此?為什麼他的一切看起來都這麼愚笨?爸爸的愚蠢害了自己,害了全家,但他根本都不知道!他又知道,我的憤恨其實都起因於這些年來的所有委屈及不安嗎?
「回來啦!」我沒回他,默默地回房間。「你能不要這麼情緒化嗎?」爸爸也火了,我也火了,轉身大聲說:「那你消失啊!」我摔了門,不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後來爸爸就從家裡消失了,僅留下那盆他平日細心照養的海棠花。
二月的時候,海棠花開得茂盛,諷刺的是,爸爸罹癌,住進了醫院。
沒人告訴我,爸爸被醫院判了死刑。
媽媽帶我去醫院探視爸爸,我到的時候,他正熟睡,手腳已經被綁上束縛帶,面容憔悴,眉頭緊鎖,整個人瘦到脫形,因為束縛帶而不安地在床上蠕動著。隨著痛苦加劇,他突然醒了過來,媽媽趕緊按鈴讓護士來給他注射嗎啡。看著爸爸這樣,我突然沒來由地開始驚慌起來,全然忘記我過去是如何地希望他死、他消失。種種不安、罪疚感讓我不知如何自處,眼前的景象,像爸爸用生命在審判我一樣。
記得小時候哭的時候,媽媽說仰著頭,眼淚就不會掉下來了。
我照做了,或許我仰的不夠高,眼淚依然在眼窩裡盤旋。凌晨三點,爸爸離開了。因為我還小,沒能跟媽媽一起去殯儀館,只能待在家裡等著媽媽。等著等著,我睡著了——夢中,爸爸站在我面前,臉色慘白,一言不發,身上像被雨水淋過。
爸爸出殯時,我端詳著他的遺容,意外地冷靜。因為他太黑了,葬儀社在他臉上化的妝,不自然的白反而使我認不太出他來。畢竟我們真正相處的時間只有四個月。自懂事起,我恨了他這麼多年,在他回家的四個月中,我同情他、恨他,卻又想原諒他。時間太短,短到難以釐清這些糾葛,他用四個月教了我其他父女用畢生學習的道理,太短太短,也太少太少。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海棠花凋零了,像爸爸,也像我。花瓣一旦落土,莖上的綠葉即便再努力運送養分,亦是徒然。
♦原作為38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國中散文組 第一名 作品
黃美金
臺東縣立寶桑國民中學 九年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