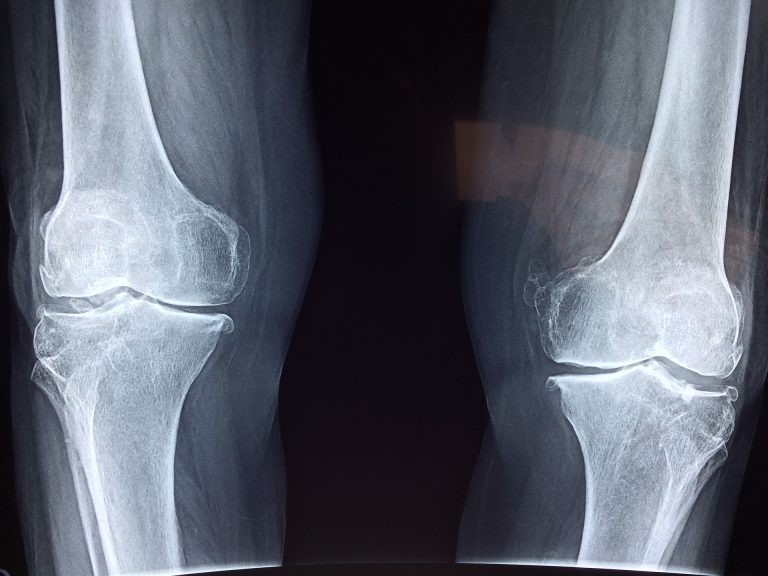家秀一如既往,在薄暮中清醒。冬天的寒風凜冽,她掙扎的下了床,穿上厚重的外套,打掃院子後,她倒了一點點煉乳在杯子,摻和著熱水,看著蒸騰的水氣慢慢調勻冷冽的空氣,再配個饅頭當作早餐,開啟了尋常的一日。當家秀騎著腳踏車往學校疾馳時,田邊院落細碎的動靜鳴奏著一天的序曲。鄉下人的生活總是在與時間競逐,一如追日的夸父,追著追著就把人衰老了。衰老的巨人一個個倒下了,下一代的孩子繼續著不完的競逐。有時候–在因為說了台語被教官罰站在國父銅像前的時候,家秀會做起白日夢,她看著每天不斷重複勞動的人們思考著,他們在追什麼呢?家秀從來沒有答案,她面前的國父銅像始終不曾給出解答,依然冷肅地遙望著彼方……。
家秀的家離學校很近,可以在午間回家吃午飯,甚至睡上一覺再回到學校。但家秀渴望去到更遠的地方。於是家秀翹課去學校後的竹林,在那裏玩耍直到夕陽西下。她看著橘紅的火球漸漸下墜到山后看不見的地方,心裡頭有膨脹起某中模糊的情感。夕陽看起來十分巨大,因為是日落之處,夕陽的顏色把整座小山籠罩了起來。
家秀總覺得下一秒整座山就要燒起來了。
「當山燒起來的時候,我要趕緊跑回家去。」家秀這樣想。然而山終究沒有燒起來。家秀舒了口氣,像是安心了許多似的騎腳踏車回家。除了夕陽和家秀心中燒起來的山,沒有人發現她的消失。家秀想像著火燒山的樣貌,暗暗覺得去了燃燒的山的自己無比勇敢。
不想讀書的時候家秀會想起小時候阿母忘記給她辦入學的事。在蘭瑪這個簡家村,郵差看到姓楊的信件,以為是寄錯了,加上村子上下都是老相識,便忘記了這封本該通知她入學的信件。最後阿母帶她到最近的小學,送進了唯一認識的老師的班級裡。老師是「酒鬼簡」,有次叫家秀去跑腿買菸,家秀卻在去柑仔店的路上遇到阿母,她還記得清尹說:「你去跟老師說,我是送你去讀冊不是送你去幫她跑腿買菸的。」後來郵差終於認識了新來的楊清尹和跟著清尹來的家秀。
「乎伊先啦!囝仔人,赫呢暗擱蹛佇庄尾,危險!」在庄頭打針的時候,叔公會讓她先打,雖然家秀也不認識這是幾叔公。
「阿這是誰的囝?赫呢暗擱來噢!」也總會有人詫異住在庄尾的家秀,在晚上自己走到莊頭打針。
「阿吉的啦!」叔公答道。
「賭鬼仔簡哪有這細漢的!」簡吉的孩子都已經長大,家秀這樣年輕的生命,在簡家村實在太過突兀。
「我是跟轎的!」家秀其實並不太懂「跟轎」是甚麼意思,只是聽著人們這樣稱呼、議論,便學會了這樣自我介紹。
「唉呦,你跟轎的喔!」聽到孩子這樣故作大人語氣的說明,眾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家秀猜測也許「跟轎」就是稱呼媽媽去了大城市的孩子,但簡志從來不被這樣稱呼。大家都比較疼簡志,簡志總是可以吃餐桌上的那支滷雞腿,也從來沒有人忘記簡志是誰的孩子。
事實上,除去多吃一顆紅蛋的特權外,家秀並不在意簡志享受到的多餘寵愛。家秀更在意媽媽偶爾帶給她的冬瓜茶,她喜歡那甜滋滋的冰涼飲料。媽媽只帶給她,也會讓她一個人喝一大杯。一直到有天爸媽吵架後,媽媽拉著她到屋後的倉庫,倒了一杯冬瓜茶。
家秀覺得那杯冬瓜茶異於一般糖磚熬出的的香甜,而帶著一股嗆鼻的臭味。她一直哭一直哭,拒絕喝下。家秀一邊哭一邊想回家,清尹卻早將門鎖上。
家秀被清尹拽往懷裡,她感覺到清尹顫巍巍的身子,伴隨著那不知是淚還是擁抱下的汗水。清尹就這樣緊緊抱著家秀。
清尹看著家秀,覺得時間過的太快了,有的時候一起床她還以為自己仍是那個住在雲林鄉下的少女。
她是那麼的渴望自由與安穩,連作夢都能夢見自己生出一對肉翅,朝著陽光飛行。
她16歲就離鄉打工,到處奔走,和又緣投又風趣的男人相愛,本以為終於找到了適切的避風港,但當得知那個口口聲聲要娶她的男人,不但已婚還早有四個孩子時,她才驚覺自以為的港灣,其實是一場劇烈的風颱。她帶著自由與富庶的渴望遠行,最後卻帶著家秀嫁到了比虎尾更鄉下的蘭瑪。好不容易擺脫了都市滿口謊言的男人,卻嫁給了參選議員失敗又染上賭博的簡吉。
不甘心啊,自己不過22歲,憑什麼被困在鄉下一輩子?自己見過城市的繁華,好歹也是有見識、才調的人,為什麼沒有辦法飛向天空?她還深刻記得剛出生的家秀,被包裹在床巾裡,蜷曲成一個橢圓的上弦月,像一滴眼淚。
一滴無法承重的淚,讓即將展翅高飛的鵬鳥重重跌落。清尹並不是不愛家秀,只是她太年輕了,尚不知道該怎麼愛孩子勝過愛自己。
過了許久,清尹緩緩鬆開緊緊蜷曲著的家秀,顫抖地拿起了那杯冬瓜茶。
「碰碰碰」倉庫的木門一陣晃動,突然被拽了開來,外頭刺眼的光線照了進來,緊跟著的是騷動的人群與不安的議論聲。
「夭壽喔,摻農藥欲乎囝仔啦!」
「清尹阿,我知影你足艱苦啦!但是囝仔足可憐欸,麥按呢啦!」家秀隱隱約約聽到幾個大嗓門女人的數落,她被緊緊摟著腦袋,在爸爸的懷裡發抖。
是簡志告訴爸爸阿母帶著家秀去倉庫,家秀在哭。簡吉略覺得不對,召集了牌友才把門撞開。一開門就看見清尹正要灌家秀喝東西。
清尹最後離開了蘭瑪,去大都市裡討生活。家秀和簡志被送去了嬸婆家,而簡吉終是因為欠下了龐大賭債,變賣的祖產、田地後,跑路了。
家秀改姓後,這裡終於又恢復成了簡家村。
轉眼已是年尾。過年的時候,一個烤玉米的攤子承載著垂涎孩子的殷切眼神定時出現。老闆在冒煙的烤台上擺放一支支飽滿的玉米,一層層的醬料在烘烤下飄出陣陣香氣,勾引、撩撥著眾人味蕾,比起老闆殷勤地吆喝「烘番麥喔!」更加吸引人。漸漸的,小攤便被許多孩子和給孩子付錢的家人,裡三圈外三圈地團團圍住。
「頭家頭家,你是按怎不先烘好再秤阿?」簡志探頭看著老闆俐落的刷好醬料,將一支烤的焦香的玉米裝袋,交到一個個引頸期盼的人手中。刷上醬料的玉米自然比原本的玉米多了些重量,但這樣的「眉角」就像是窗紗,遮掩不住什麼,但總是不便點破。也只有童言童語又鬼靈精怪的簡志,口無遮攔地把窗紗扯下。
「你遐昵巧,你是幾個老爸生的阿?」老闆娘不甘示弱的還以顏色,家秀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從老闆娘跋扈而兇悍的口吻中,她意識到了弟弟被人欺負了。
而且是被粗鄙的言語辱罵了。於是她回家告訴嬸婆,嬸婆怒氣沖沖地趿起藍白拖,抓著兩個孩子便直奔市場。市場還沉浸在過年的熱鬧與溫馨中,嬸婆一句高音的「阿汝欺負囝仔是足有意思嗎?」立刻點燃了比攤販附近的高溫更驚人的騷動。兩個女人在玉米烤台前你一言我一語,不甘示弱的過招,最後嬸婆以一句「他幾個老爸生的你就是幾個老爸生的!」贏得全場的歡聲雷動。家秀還記的那天晚上,她和簡志都拿到了一支香甜飽滿,滋味十足的烤玉米。
對家秀而言,嬸婆是所有人中最溫柔、卻又並不柔弱的女人。剛來嬸婆家住的時候,同學指著他說:「你爸爸是賭鬼仔!你媽媽去作小姐!」家秀憤怒地向同學揮拳,但嬌小的她實在無法造成什麼影響。最後家秀紅者眼眶,不顧一切地跑向火燒山,在山頭面對夕陽揮拳撓髮地咆哮。
傍晚回到嬸婆家後,「阿汝是走去兜位?」看著家秀回家,嬸婆皺緊的眉頭方稍稍舒緩。
「按呢阮會煩惱欸。」嬸婆看著家秀哭腫的眼睛,一邊給家秀擦淚,一邊摸著她的頭說。嬸婆一聽家秀的描述,便皺起眉頭。
嬸婆瞪大眼睛,用力地拍了拍她的背,像是將鄉下人的勇氣與衝勁灌注到了家秀體內。「你騎腳踏車去,跟他吵架!」那個暗暝,家秀騎著大人的腳踏車,在漫天星斗下夜行。家秀邊騎邊想著嬸婆橫眉豎目、憤慨不平的要她去和人理論時,那種氣勢凌人的架式,那種充滿生命感的力道深深的震懾了家秀。前方沒有路燈的田畦,似也漸漸明亮起來。腳踏車的尾燈照在後方的山上,一管細細的紅色光線,像是正在點燃山腳,但山頭卻是廣大浩瀚的星辰。家秀想像著自己的夜襲,征途是浩瀚還與中的星辰,使她莫名地興奮了起來。
就在家秀拿下屬於自己的勝利幾天後,嬸婆教她搓元宵。
「吃圓仔,長歲。」嬸婆手法純熟,不一會兒便搓出一盤渾圓精巧的紅白珍珠。家秀仔仔細細的模仿,方搓完一盤。她一抬頭就看到嬸婆正對著她文文的笑,雙眉彎彎的,宛似菩薩定定地看著她。
家秀突然被這帶著悲憫的神情攫住,眼淚開始如水龍頭般不受控制的滴落。
「唉呦,囝仔人哪會講哭就哭?」家秀把臉別開,深怕眼淚落到元宵上。
「汝真巧阿,做甚麼攏足巧!」嬸婆一邊給她擦眼淚一邊說。「遐昵搭心擱遐昵𠢕。」家秀哭得更厲害了。
「好阿,麥哭阿。來搓圓仔。」家秀臉上因為擦眼淚而沾上了糯米粉,一塊塊縱橫交錯的白色顯得格外滑稽。那一瞬間,家秀腦海閃過火燒山的形貌,她想起山頭曾經被夕陽照耀的那麼紅。但現在家秀無比地篤定,她的山是再也不會是火燒山了。
那年元宵節家秀吃了特別多的湯圓。挑著鍋裡紅色地湯圓吃,因為嬸婆說紅色的湯圓吃了嘴唇紅紅的「查某囝仔特別媠喔!」。家秀也想把白湯圓留給媽媽,因為清尹曾經對她說過「一白遮三醜」。直到晚上孩子們拿著花燈四處晃走的時分,家秀看著黑暗深處接二連三亮起的火光發起呆來,像是要被深夜裡的磷火吸引一般。
簡志問:「阿母甘ㄟ轉來?」
正月總是帶來了意料之外的驚喜,正當家秀以為清尹不可能回來時,清尹拖著一只行李箱從初春燈火交織的彼端朝她姊弟走過來。
「阿母!」簡志立刻興奮地向清尹跑去,撲在她的懷中。清尹抱著簡志,走到家秀面前停了下來。在夜空中滿月的照耀下,她們就著樣凝望彼此。
「阿母。」
「阿秀,汝大漢了,要照顧阿弟仔,知否?」
「我知。」家秀紅著眼眶,只覺得喉頭一陣酸澀。清尹輕輕把簡志放下,說:「住在嬸婆家,要聽話喔。我會足久才會轉來。」面對著遲來地叮囑,簡志似懂非懂的點點頭。
於是清尹笑了笑,轉身。就在她慢慢地走了幾步後,家秀說:「媽,我沒錢買蠟燭。」
清尹回頭,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鈔塞進家秀的手裡,家秀的眼淚立刻奪眶而出,淌濕了手中的國父。家秀在朦朧的視線中看著清尹的背影慢慢地越走越遠、越走越小,最後在巷口轉角的路燈中消失。
家秀猛然想起了那碗早已糊掉的白湯圓,開口大喊。
「阿母!」
♦原作為106明道文學獎 高級部短篇小說組 第二名 作品
張天馨
高級部二年級